纪念|弦:家乡杨庄营
编者按:著名诗人弦于温哥华时间10月11日上午去世,享年92岁。
201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弦回忆录》,记录了他对家乡河南南阳的回忆,参军的过程,军事生活,以及许多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相遇的名人。本文选自《杨庄营》中的一个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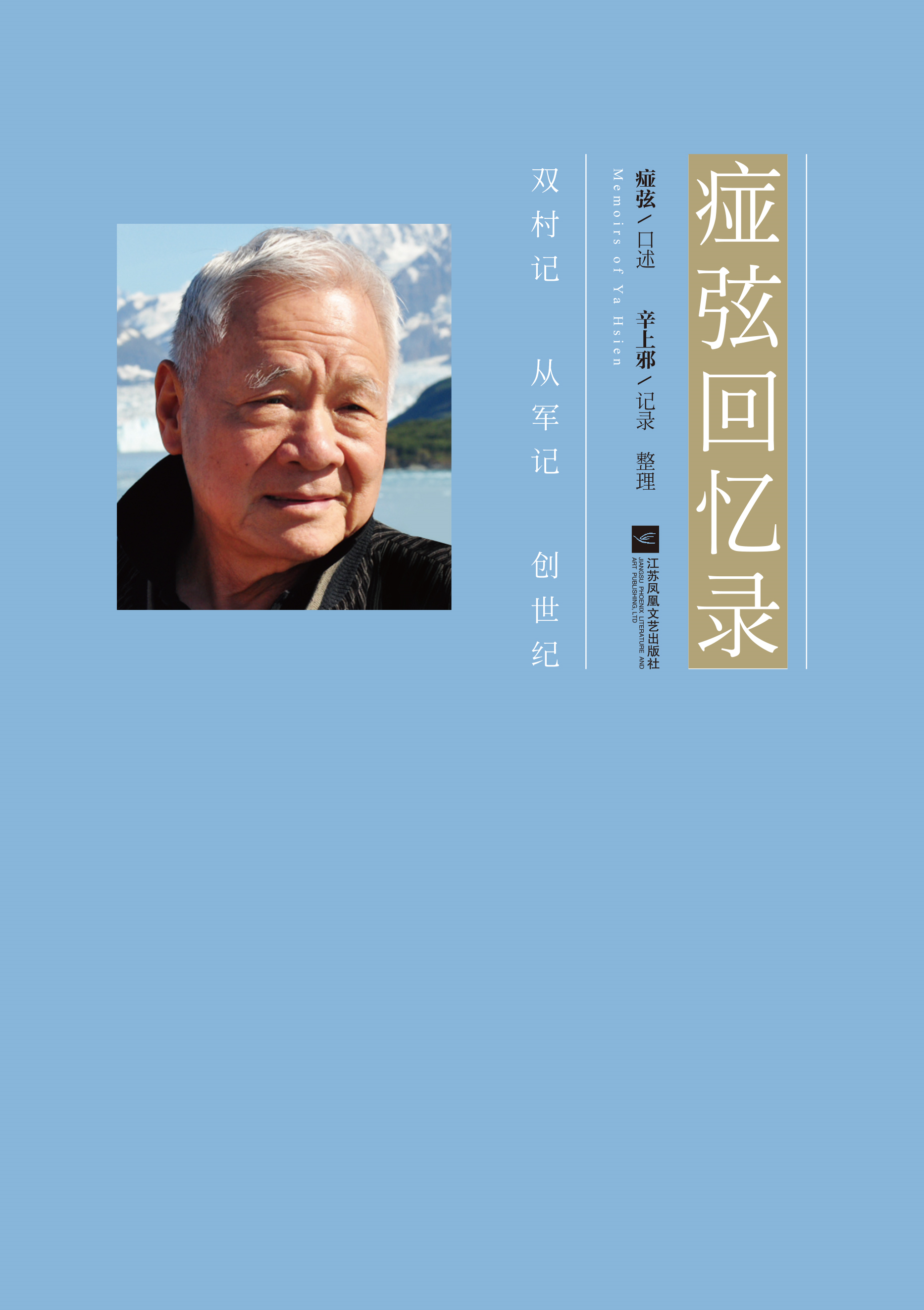
《弦回忆录》书封
与姥姥家不同,我的祖先非常痛苦。苦到什么程度?那是清朝时期,大年三十,我的曾祖父家里连一点面,一粒米都没有。曾曾祖父去市场卖门神,春联,灶王爷。有些孩子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饿得前心贴背,以为爸爸回来肯定会带食物。结果一个都没有卖出去。一家人只能抱头痛哭。后来他们借钱,在官路旁边开了一家鸡毛店,叫“冷店”。门口放着一个草筐,里面放着馒头,盖子上放着一个馒头,说是卖馒头的。住在河南的客栈里,不需要钱。河南人很老实,说:我们这床被子让人家盖一夜还要钱?这个又盖不烂;睡在地上还能把地压一个坑啊?所以不好意思要钱。但是“住店不住店,先吃一碗面”,那碗面吃不吃都要收钱。那碗面钱就是店里的钱。曾祖父比这更惨,我只能卖个馒头,让人喝碗汤。五个孩子只有一件外套,谁出去走亲戚,谁就穿这件外套。
有一天,一匹马远远地走过来,这匹马渐行渐近,仿佛马上就没人了。走近一看,有人立刻伏在地上,头都快靠在地上了。摸摸他的头,病得很厉害。有几个小孩把他扶下来,发现他已经胡说八道了。幸好我曾祖母会针灸,治好了这位官员。官员一觉醒来,烧也退了,病也好了。看看他们家的大小真的很穷,太苦了,这个人说他住在杨庄营,姓华,为了感谢他们,让他们去看看他家的坟墓。所以我不怕鬼,我家是看坟的出身。从那以后,我家的院子就是一个墓地,香火已经断了。院子里种着李子树,孩子们在院子里吃李子,跑来跑去玩虫子,一点也不害怕。
杨庄营的房子古朴典雅,十分美丽。杨庄营有300多户人家。他们过去住在杨,所以被称为“杨庄营”。然而,在明朝,他们被杀死了九个家庭,剩下一个去外县姥姥家走亲戚的孩子没有被杀死。这个孩子后来有一些后代,大约有四五个家庭,其中一个还是我们村的小学校长。姓华的富人接受了杨庄营的房子。现在明朝还有几栋房子,青堂瓦榭,五脊六兽。我们的祖先在墓地旁边盖了一个小庵子,给别人看坟墓。与华家豪华的房屋相比,我们看到墓人的房屋要简陋得多。这五个孩子是我的曾祖父,后来他们自己种地,买地,变成了小地主。当我记得的时候,我们有一瞬间(一百亩),已经把田地给别人种了,但是我们农民的习惯还是一样的。妈妈还留着一块地自己种,就在我们家后面。在离厨房近的地方种一些青菜。有时正在做饭的时候,妈妈让我去摘豆子回来。午饭时吃我摘的豆角。
我的出生地不是在杨庄营,而是在冢头村。因为墓头有寨子。寨子是一个土城,是由当地人集资建造的。就是修土墙,把村子、镇围起来。还记得小时候见过修寨墙。每个家庭都画好每个家庭负责修理的界限,富人请人修理,没钱的人自己修理。在修墙的时候,把土里面掺上草,做成泥坯,再一块块砌成墙。寨墙有四个寨门,寨墙外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有的还种了有刺的灌木(别名玫瑰),叫“月月红”,相当于铁丝网的功能。晚上把寨子门放下。寨门关闭后,一般不允许陌生人再进来,只有认识的人才能进来。寨子里有民团守护。人们还有土枪,土炸弹,刀箭。一些地主还邀请了长工或者很多会武功的人来值夜。晚上看管的时候还要联系。太阳下山后,点一股香味,一股香味完成后再点一股香味。香味是线香,但并非插在那里,而是一根一根斜放,首尾相接地放在香盘里。香盘上覆盖着厚厚的香灰,香放在上面也能燃烧,不会熄灭。一个烧完了,下一个就被点燃了。那时候没有钟表,执勤就是按点几根香来计算。比如约好,两根香后吹羊角。羊角是羊角,吹任何声音都是约定的暗语,用不同长度的声音代表各种情况。另一个哨所听到羊角声,也会回答。晚上经常听到号角的声音。那声音在夜晚听起来荒凉而凄凉,有时号角声引起一片狗叫,特别可怕。有些富人还修建了炮楼。晚上住在炮楼里,家丁把守。把土枪、炸弹、滚木石放在炮楼上,就是避免匪徒晚上来。有钱人在寨子里盖房子或租别人盖的房子。平常住在自己的村子里,匪徒来了就跑到寨子里去。从明末开始,我们就是刀客出没的地方。刀客就是红胡子,匪徒。在闹得太厉害的时候,寨子里的民团已经抵挡不住匪徒了,大家都跑到城里去了。城里有国军,警察,比较好。但是城市的生活成本比较高,我家基本上还住在寨子里。
土匪和土匪之间也有战争,以大吃小,有分有合,其中的恩怨真是犬牙交错。老作家姚雪茫是我们邻县的,他的经典小说《长夜》就是对土匪的描写,写得非常成功。他对匪徒的认识非常深刻——对于一个善良的农民是如何成为匪徒的,研究也是最深入的。他认为是因为饥饿,跟着“刀客”有吃有喝。刀客到村里就让村民买多少枪,说他们要枪来维护当地的治安。假如买不到枪,就要折算多少钱。还有一些妇女被刀客抢走了。对姚雪茫最深刻的描述之一是,那些女人有些没有定力,到那里吃香喝辣,过一段时间就不愿回家了。回家饿饭嘛。所以,当家人根据歹徒的需要用钱赎回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想回去,但是很难说出真正的原因,所以他们假托其他原因,比如“你二哥对我不好”等等。他写下了人性的所有弱点。
到了晚上,村里听到狗叫的声音不一样,大家都很紧张,都畏缩在自己家里,害怕得厉害。假如狗叫得很凶,那么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村里就会传开,昨晚哪一家被杀,哪一家被抢。狗叫是不祥的征兆。一直到现在,半夜听到狗叫,我都会害怕。还有一种叫做“打业”的,就是仇家之间互相报复。又是在夜晚,仇家互相砍杀。那时候已经没有法律约束了。农场主没有饭吃,也跟着匪徒跑。到了之后就不能再回来了,因为做了坏人,没有回头路。但是匪徒大多是无赖、小人,良民还是跟着少数。
家家户户都有枪,匪徒来了还能应付。在欧洲,我家有一支枪,也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不知如何销往中国。这把枪叫做“十大响”,可以连续放置十发子弹,就像机关枪一样。那时候还没有机关枪。这种枪有两种枪,一种是装要发的子弹,另一种是装没发的子弹。一次可装十颗子弹。前弹一发,后弹就进入枪膛。子弹头是铅做的。人们中枪后带出一块肉,伤口溃烂,后来国际上被禁止使用。看起来平乐村没有枪,杨庄营很多人都有枪。那“十大响”我小时候还玩过,比我高。我买的时候,枪里有几颗子弹。我爸爸拿着它给邻居看的时候,不小心走了,在屋顶上打了一个洞。每个人都看起来很灰,每个人都很害怕。之后父亲又买了一个“盒子炮”,是手枪,四面八方的形状,长长的枪梢,还有一个木盒,是德国制造的。行军时,他可以把枪放在盒子里。盒子也可以放在枪托上,看上去就像后来的卡宾枪,但实际上还是手枪,一连可以发射二十发子弹。上面有一个红穗子,过年的时候放在香案上还要拜,让枪庇佑全家。
主张农村自治的学者梁漱邈的几个实践学校的学生,在20世纪30年代在内乡、镇平、淅川县发展地方自治——用法家的方法,也符合现在用所谓贤明独裁的方法治理豫西,治理到夜不闭户,路不捡遗。她们的方法很蛮,就是司马中原《荒原》所写的那些方法。据说为了以身作则,县长出去演讲的时候,带了一个被判死刑的犯人,去演讲的地方敲锣,聚集了几百人。所有的村庄都来了。演讲结束后,县长当场用带来的青铜割伤了死刑犯,“谁不懂事就是这样”。那时候的专员是彭禹廷,他以身作则,主张修桥修路,废除坏习惯,深受人们的喜爱。法律执行也相当严格,偷一个苹果都有可能被枪杀,还规定不能拉鞋子走路等等。从豫西开始,在高速公路两侧种植绿树。用这种方法竟然也把豫西治好了。
由于年头惊慌,闹匪徒不稳定,我们搬到冢头去住。当我爷爷回到我们原来的村庄去分场时,住在朋友华公台家里。华家有炮楼,有家丁把守。晚上,爷爷感到天气躁热,便说出去转转。根据村里的人说,爷爷在散步时遇到了歹徒。爷爷跑了,一群歹徒追着他,他掉进了一个很深的空粪坑。北边把人、动物的粪便全部放在坑里,加上土壤的肥料,再把土块取出来送到田里去肥料。等到他爬上来,就被匪徒抓住了。听见爷爷大喊:“大家都要钱给大家!每个人到底想要什么?”第二天看见周围池塘里的水都是红色的,他被匪徒杀死,尸体也没有找到。直到现在,我祖父的坟墓里只有他的衣服。父亲、叔叔都想为父亲报仇,都学会了“红枪会”——白莲教的余续,又称“硬肚子”,刀枪不入。可以根本不知道找谁来复仇。后来父亲和堂叔都考上了农村简易师范。
我爷爷叫王子修,也叫王乐身,后一个名字用得很多。我父亲叫王文清,我叔叔叫王文洁。我爷爷那一代是乐字代,我爸爸是文字代,我是庆字代,我的孩子是景字代,下面是怀字代。后面还有几十句“乐文庆景怀”。回到家乡后,请书法家写下,挂在家乡的正屋。爷爷去世几年后,我出生了。我父亲是长子,我是独生子女。我出生的时候,父亲觉得家里一片黑暗。他希望我的出生能给我的家带来光明,给我取名为“明庭”,然后给我取名为“庆麟”。因为父亲发现我应该是庆字一代。在高大的时候,我开始使用庆麟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明庭”这个名字。海峡两岸开放后,我回到家乡,问堂弟:“我看见我的家都变成了废墟,老房子都塌了,能不能再盖起来?要多少钱?”堂弟说,大约20,000元。我花了十五万台币,把原来老房子的砖土都用在里面,盖了一栋楼,十一间房。我用“明庭”给这个院子取名,请朋友、书法家董阳孜写的字,刻上一块匾额挂在前面。
我们家有一张老照片,是我们家的全家福,可惜后来没有留下。把我放在照片中间——第一个男孩嘛。那时我还年轻,后面还用枕头垫着坐着。照片中有奶奶,父母,叔叔阿姨。这张照片的底片是玻璃,人脸都是红色的——过去人们说“照相吸血啊,你看那玻璃上的红色就是人血”。底片易破,要小心存放,但大部分都破了。最有意思的是,当拍照的人来家里拍照时,他们来自南阳城,带着相机和风景,搭起一个架子,用黑布遮住草堆、门、四合院、房子等。他们觉得拍照的背景会是黑色的。没想到草堆和四合院会更有活力。那时候就是那种风气。照相馆里全是假画儿,连家具都是画出来的,其实那时候老家具还是很多的,摆个老家具就好了。
只剩下一张我母亲的照片,爸爸没有照片,现在我都记不清他的样子了。一九四九年后,我母亲的照片被拍下。我的堂弟说,有一天,照相馆的人来学校给孩子拍照,村民交点钱也可以拍照。堂弟看到我妈妈已经很虚弱了,担心她很快就去世了,就带她去拍照。妈妈说:“不照,生病了,照了也不好看。”堂弟哄她说:“照片不好看可以不要。”这张照片上,她看起来很紧张,好像不知所措。当我回到家乡时,堂弟给了我这张照片。长得像妈妈一样多一点。曾有一位画家朋友给我画素描,画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完全是记忆中妈妈的样子。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