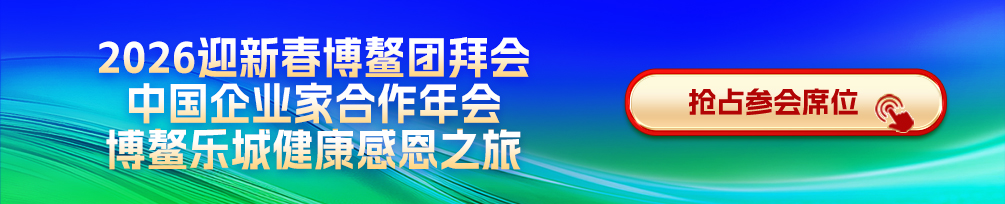人类事务,心事,亲身生活——2024年《人民文学》青年小说读书
年度文学杂志阅读邀请中,青年写作以其新鲜、立诚、幻变的新品质,往往是最令人向往的模块。2024 2008年,发表75周年的《人民文学》继续挖掘和培养新人传统。年轻作家不仅活跃在常规板块,还通过多个渠道形成推荐新一代文学的协同努力。专门为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文学》中的作家设立的老牌频道“新浪潮”,今年迎来了马林霄萝、张哲、薛玉玉等近20张新面孔。2024 年 9 月,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人民文学》还特别推出了“青年新作辑”,发表了吴越、孙孟媛、崔君、渡澜等八部具有不同实验色彩和风格的新作。此外,自 2020 2008年开设的“写作课”频道,作为高校创意写作教学的优秀窗口,今年推出了王译彬《壁听五月》和陈王言诺《如果每个人都不知道下落》两期,苏童和李洱分别给予指导和分析。从" 85 后"到" 00 后",2024 2008年《人民文学》带来了40岁以下朝气蓬勃的作者梯队,成为我们在青年创作现场捕捉新风信的重要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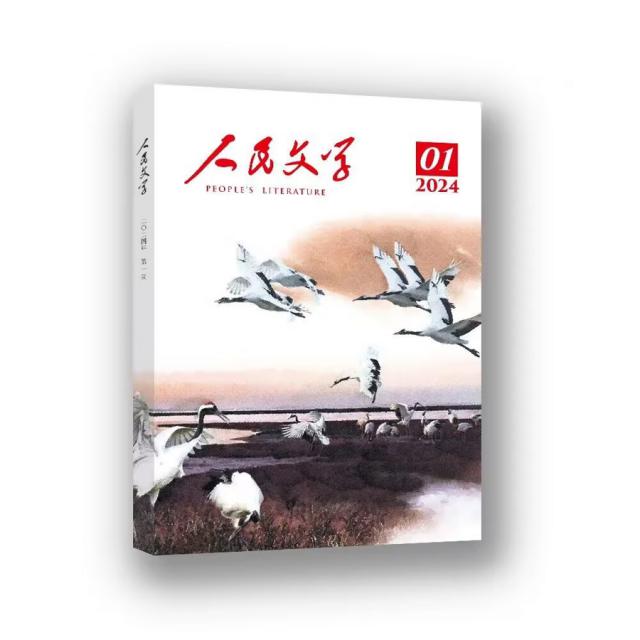
《人民文学》
"无限的距离,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
“人间事”可作为观察这些青年小说的锚点。大多数小说家选择从别人的想法和烟花世界中获得灵感,表现出取法现实主义的自然和自觉,无论是对世界人心的勘察,还是对传统文化的镀亮。李知展《望春门》以深情的笔致,讲述了豫东平原上李霸两大家族半个世纪的恩怨纠缠,牵连出一起未完成的陈年罪。回到家乡扫墓的女儿程念,把目光投向了父亲刑警老程和雪湖镇牛肉煎饺店老孟的一生友谊,梅姨的母爱和恩欠,比如雪落在深湖。除了当地历史大开大合的人才之外,老程和老孟愿意渺小孤独的英雄凡人歌曲是女儿想从父母那里接过的“生活方式”。理想的民间人格,在普通人的淳朴和善良中,也在孤独的饮食味道中——老孟的牛肉煎饺被野心勃勃的家庭打开,但世界上很难找到耐心和孤独滋润的味道。
许多作品都描述了加速发展的现代经济对传统产业的影响。旧技艺如何消失,藏污却充满活力的民间世界如何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耐人寻味的不是这些不新奇的主题本身,而是以“追溯传统”为写作行为的年轻人透露出的主要状态和内在动机。马林霄萝的《高歌高歌》获得了饱满明亮的京腔京韵,再现了宋家四代人手中“西四最后一家洗浴俱乐部”的百年盛衰。从热气凛冽的俗世魅力,到城市拆迁改造中的歌曲结束,都是时代造成的。由于储水修坝造成的河流萎缩,在森林的《鱼史》中,渔获急剧下降,“莫家传承数百年的钓鱼古方就此被判死刑”。钓鱼的名门流水风光,最后都付之苦涩的笑声和叹息。林为攀的《便携式祖先》以纪实片脚本的形式,再现了“我”看爸爸如何顽固地重建族谱,解开人生之谜的全过程。小说试图再次结合“我”与土地根系的纽带,但为什么“爸爸寻找父亲的过程也是我寻找自己的过程”,直到最后还是让人怀疑。

李知展,马林霄萝,森林,林为攀登。
在这里,年轻一代追溯家族、地方、民间的源头,想要定格“最后一个”远去的文化身影,似乎是四十年来寻根文学的隔空回响。假如说 20 世纪 80 在现代的参考下,年中的“文化寻根热”再次亮化了当地的文化和民间传统,从而重申了第三世界文学的本位性和主体性。然后,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年轻人的叙述,大部分都停留在世事沧桑的旁观位置——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通过漂浮在一边的“听故事的人”说出来的。回到家乡后,他们总是离开家乡,也不再对“最后一个”报以过度悲哀或浪漫的挽歌立场。如何利用“旁观之眼”翻出新品质,带来更大的挑战。我认为,年轻一代所表征的怀旧、收获和失落,可能是希望在想象和追踪中,复活一个曾经更慢、更有尊严、更有活力的世界,从中获得和吸收这一代人如何“亲自生活”的养分。在那里,味蕾可以复活充足的食物味道,灵魂和筋骨皮肉可以由内而外被洗澡水烫得松弛伸展,有声音,有光泽。对于预制菜、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生活,这是一种抵抗吗?当过快的现代节奏反复降低和退化人们的感知时,如何找到差异化的感官能力和身心态度,可能是他们“追溯传统”的深层意图。大规模的流动和离散经验塑造了越来越多的个人脱离国界。在这里,对熟悉感和确定性的需求,对真正被赋予和附着的生活的需求,都成为寻找一方“再嵌入”天地的文学驱动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令人不安的陷阱:除了“听故事的人”之外,他们的主要位置也可以在哪里?假如作者内心的自我和叙事目标缺乏真正的对话,就有可能停止与文学史传统的对话。对早已迁离农村故地,甚至从未有过乡土生活经验的年轻创作者来说,“旁观之眼”也许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问,除了强烈的地方审美定势之外,他们与文化传统、山川大地的对话方式是否还有其他概率没有被激发?
表达别人的心事没有对错。在年轻人的写作现场,“无尽的距离,无数的人,都和我有关”,从来没有陷入过姿态和空话,甚至一次又一次地磨炼着迎接复杂和突破自我界限的决心。举例来说,在今年的作品中,中老年妇女的外在生活和内在世界的延伸,可以看到杨天天的《浅生命》、崔君的《小山的阴影》、王译彬的《壁听五月》和薛玉玉的《对方在输入》等多篇文章。年轻女性作者在女儿、母亲、妻子、姐妹的数重身份织体中,对女性多义生活的可能性,做出了不同的挖掘和支撑。

杨天天,崔君,王译彬,薛玉玉。
与其靠观念写作,不如像蚂蚁一样不顾一切地前进。
事实上,真正的对话,总是以各种各样的自我开放,甚至自我暴露为前提。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没有被共识净化的新现实时,首先要考验的是小说家“亲身生活”的真实感受;其次,是虚构能力的竞争。所以,无论是天真、傲慢还是贫穷,那些愿意以“自我担忧”诚实面对当下的年轻人,总有一些闪光点是不愿意错过的。其中,陈萨日娜的《在承天寺》是一篇独特的文章。一对游魂野鬼般的都市异乡人,各怀沉重的秘密,在中秋夜相遇、漫游,在人山人海的地铁站挥别。小说跨越时空,让两个一面之交的年轻男女与苏轼和张怀民形成叠印,苏轼和张怀民在《天寺夜游记》中“但闲人如我的耳朵”。陈萨日娜对轻盈浮动的月光进行了一个奇妙的当代比喻:没有月光的地方,但不再是古人的月光,而是陌生人社会中失眠的现代人真正敞开心扉,成为治愈彼此的月光。对于那些向陌生人坦白的自我问题,比如坠入深海的成长创伤,难以实现的痛苦的艺术梦想,第二天还是会到来。但是好好活着,继续面对,“前进,不要留在这里”就是最好的答案。
在孙孟媛的《蚂蚁爬行》中,还有一位没有名字的女主角“她”。“她”带着天真的婚姻想象去南洋试婚,最后从幻觉中惊醒,看到了自己生活在观念和符号关系中的真相。外国出租屋里无孔不入的蚂蚁,由于其恐怖的集群生命力,暴露并最终毁掉了早已空空如也的爱情。甚至蚂蚁也知道如何遵循本能,敏锐而顽固地死去,而不是压抑食欲和烟火欲的人。虽然小说中可能会有概念解读的痕迹,但最后一个只有“她”看到的闪电,“划破夜空,劈开眼前的混乱”,也被读者看到。它还构成了一个具有自反性的提示:与其依靠观念来生活或写作,不如像蚂蚁一样不顾一切地前进。
张哲的《葡萄园》奉献了“我”的表姐夫陈无疾,一个以人格打动读者的文学人物。他谈到了葡萄种植时闪耀的表情,令人难忘。现代文学中的人物衰微已久,所以更为罕见。小说家们选择了一种有规律的叙事方式,其中形状和质量的张力是巧妙的,因为陈无疾一生都被“变数”和“不确定性”所吸引。这一不规则的他,最终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曾经抱紧确定性和安全感的“我”。“我”对陈无疾有一种细致而复杂的感觉:夹杂着对表姐和外炔女的羡慕,与表姐夫分离的“表亲加姻亲”,既想信任,又忍不住疏远别扭。张哲以诗意的天赋,将独生子女成长中远未定型的自我推向“不确定”的一面。正如我在小说中跟随陈无疾一前一后,从葡萄园走向现实世界一样,“我们周围不再是一个缓慢而虚假的湖泊,而是一个充满隆隆声音的现实世界”。对于血缘亲疏的迷思和张力辨证,同样出现在李淞的《失寻之夜》中。小时候被父亲抛弃的恐惧,长大后变成了对父亲的连年逃避。从童年的洪水到面前的蟹塘,“我”又被水弄湿了,“领悟的时刻”意外地借着朋友的儿子来了。背上的“小心脏从我身上跳来跳去,体温很薄”是另一个年幼的孩子软弱无条件的依靠,取代了稳如泰山的爸爸的威权,为“我”补上了迟到的情感教育。

陈萨日娜,孙孟媛,张哲,李淞。
看完这篇文章,我们可能会突然明白,为什么很多年轻人要用“家”的粉碎来表征和构建一个“需要修复的整体世界”,为什么很多人的烦恼总是围绕“缺失和填充”反复上演。这些小说,最终汇入了一个充满青春的问题:是什么构成了我们?到底为什么我们是完整的?在现代主体破碎分裂的成长语境中,“完整的自我”不再是预先构建的教谕或承诺,也没有人能被动地在同一个地方等待兑现。作为一种积极寻求完整道路的方式,文学凝聚了人与人之间最小单位之间不断的联系、断联和再联系的努力。一代人文学自新的概率,在更大的模块中,从不在别处,而是亲自生活。对于这一切,我想,未来将继续给我们一个新鲜、立诚、幻变的答案。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年教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