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的精神病人③ “橡子”的归处:这个工作室抓住了他们。
【编者按】
在中国,大约有200名严重的精子症患者登记在册。
他们在哪里?除了生活在精神病院的病人和媒体报道的伤人案当事人,我们似乎对他们视而不见,避而远之。
所以,他们躲得更深了。家庭要付出闭门护理的代价,医生要靠得更近才能获得信任。本报记者在整理资料时发现,这些患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仍然可以被社区和家庭接受,甚至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后来,患者被认为失去了工作能力,整天呆在家里,病情恶化,家庭被拖入贫困。
从10月29日起,我们将连载三天,用三篇报道与读者讨论如何走出家门,如何为精神病人缓解疾病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三年前,杨如梦在贵州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做实习社工,帮助可以出院的患者联系家属——一名患者才三十多岁。他早些时候在疾病发作时聚在一起打架,但他已经“正常”恢复了。因为“没人认领”,他在医院呆了很久;最后,是我哥哥来接他,看起来很无奈。杨如理想地告诉他和病人住在一起的注意事项。他哥哥似乎不感兴趣。他只问“签名会不会被人知道?”他害怕在社会上与精神疾病有关。
有些家庭成员态度温和,但听得出他们气馁了。杨如梦说,如果病人刚刚生病,他的家人会关心“他现在的状态如何”,一些反复生病的老病人不会被家人问及。
宁波康宁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文章中分析了2013年至2015年该医院的2947例出院病例,发现这些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次数越多,平均住院时间越长,患者离开医院似乎越来越困难。
即使病情稳定,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仍有可能残留疾病,不仅需要家庭长期护理(① 为什么护理人员不愿意开门?)、随诊需要基层医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② 在家中“交叉感染”不良情绪时,社会还需要建立一个适合自己的承接空间。
出院就离婚
2022年,杨如梦在贵州大学读心理学研究生,看到一家公益组织正在寻找医疗社会工作者,住在精神疾病康复病房,抱着实践心理咨询技术的想法。
她承认自己一开始很紧张,怕病人打她。但是开始工作后,她也觉得这些工作对象“像个孩子”——当时是“新冠肺炎”疫情。原来公益组织在病房接受园艺治疗,因为无法聚集而取消,所以住院生活很无聊。当病人看到社工来了,他们会围着她问:“你什么时候送我回家?”
杨如梦有一位男同事,和病人相处得很好。到了病房,他会被病人抱住:“你来看看我们,太棒了。”
杨如梦问了一些患者出院后的想法。有人说回工厂工作,有人想继续上学,有人先在家养病。何新的想法是和妻子离婚。他患双相情感障碍的直接原因是他和她大吵了一架。生病后,他在街上游荡,警察把他送到了医院。除了离婚,何新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他觉得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挤兑,别人会觉得他疯了。
在毕业论文中,她描述了自己为何新做心理咨询的过程。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u200c阿尔伯特·埃利斯的说法,杨如梦对何新解释(Albert Ellis)情感ABC理论,一个事件A可能会激发非理性的信念B,导致情感C。比如患双相情感障碍就是一个事件,“这辈子结束了”就是它引起的非理性信念,导致他不开心。
何新说:“我觉得我的情绪会经常变化,一会儿感觉很不舒服,一会儿又觉得没什么,总觉得不受自己的控制。
杨如梦说,在他心目中,从生病到被社会抛弃的逻辑关系是坚定的,这是不合理的。她会告诉他——虽然有些病人患有疾病,但他们仍然努力工作,追求个人意义,有些人会帮助其他精神疾病患者。
经过三次心理疏导,两人改变了身份,杨如梦扮演病人,何新扮演社工,等于何新劝说自己。
何新问:“你觉得在这个社会生活很艰难吗?”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真的很难。本来我会对生活抱有期待,但是自从我得了这种病,反复住院后,我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期待。我觉得我在别人眼里是另类的。”杨如梦说。
“也许这只是你自己的看法,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何新像样模仿。“虽然有些人会有偏见和歧视,但我们可以改变对生活的态度……”
这间工作室没有人全勤
经过几次心理疏导,根据量表,何新的悲观厌世情绪有所缓解。
现在,杨如梦已经毕业,成为了一所大学的辅导员。坦率地说,她在医院的工作时间太短了,她遇到了一些比较困难的案例,没有得到他们的信任。何新虽然话不多,但如果他主动问,他愿意分享,而有些患者对医疗和社工非常警惕,不想多谈家庭,有些人干脆撒谎。他们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暴露了自己的家庭背景。
根据杨如梦的理解,这并不一定是疾病的症状。也许这些病人以前有过一些受伤的经历,使他们难以信任他人。
病人回到社区,要继续面对病情多年造成的其它心理问题,如自卑,还要与残疾人相处。
2010年,南京原生艺术中心成立。这个机构的日常工作是为一些精神病人提供一个帮助他们绘画的场地,一些绘画是由中心出售的。在这里工作室画画的人有些“艺术家的脾气”,就像他们的作品一样,风格多变。
经过治疗,一些患者可以恢复良好的认知水平,但他们的意志不时变得冷漠,社会化成了巨大的压力。这里没有人能“全勤”画家。
天气不好的时候,小鹏不想去工作室。他总是吃药,工作内容也是静静的画。但是最近几天有点胆怯。
在他生病之前,他学习很好。妈妈李佳放弃了晋升,以便花更多的时间和他在一起,劝他出去。这时,她不得不感到无聊,想:怎么了,为什么病不好?
他抑制住了嘟囔。
“就像爬杆一样。”李佳描述了精神病人的康复。如果他不坚持,病人会慢慢滑入自己的世界,成为普通人中所谓的“怪物”。前面的努力将是徒劳的。所以,当小鹏表现出不想出门的样子时,她决定 “忍受”。
她说,如果她以前不明白,她会向小鹏展示她的焦虑。现在,她多说几句,然后出去散步,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第二天,她向儿子反思自己,几个家庭互相道歉。
等一家人克服困难,走出家门,小鹏坐在工作室里,面前有200支彩笔供他自由使用。他的心也定了下来。
他会画出一些华丽而具体的想象——针管里有玫瑰色的粗糙悬崖或紫色的宫殿序幕,但它们仍然是一组针管。折扇的顶部有一张昆虫的脸,看起来像是愤怒地看着画外,但它仍然是一把蒲扇。

小鹏的作品,一组针管
与李佳交谈时,小鹏把画好的折扇用来给母亲,简单地解释一下:“很古老的感觉。

小鹏的作品,一把蒲扇
该组织的创始人郭海平说,该组织从不指导这些画家。他会提出一些建议,但他们可能不会接受——这时,他走过来研究这个蒲扇,说画得好,商量了一下,问:“以后试试,只用黑白?”
小鹏拒绝了,说他最近状态不好,很难集中注意力:“我用意志力坚持下去。”
“苦恼”重新开始
在这里,小鹏和他的“同事”有创作自由,偶尔也能卖出自己的作品,分成几部分。在郭海平的观念中,客户为绘画买单,意味着他们认同绘画得好,而不仅仅是基于对弱者的怜悯。
这些画家的每一部作品都应该归档到图书馆,并且有一个数字。南京原生艺术中心连艺术家都拿不走自己的画,担心随意放在一边或者送人,于是逐渐把艺术当成消磨时间的涂鸦,不再当回事。
在这种模式下,组织的承接能力非常有限。据郭海平介绍,到目前为止,只有200多人在这里长期绘画;资金也很紧张。除了卖画赚钱,组织只靠社会捐赠来维持运营。7月,他在一次采访中说:“下半年的工资还没有定下来。”。
然而,他宁愿保持这种模式,也不愿向病人收费。他认为,如果这个人把绘画当成一种需要付费的治疗,他们可能仍然只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他们的心态很容易崩溃。
这类人常常被社会教导为不完全的人,他们要么反抗,要么接受,要么麻木。
一位父亲告诉郭海平,在孩子接触绘画之前,家里的气氛一度很差。他让儿子往东走,但他往西走。他想让孩子洗脸,需要给儿子绞毛巾。
如果你在管理严格的病房呆的时间太长,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亮表示,要全力追求“调节情绪”,消除疾病带来的情绪变化。时间长了,人会失去任何情绪。
杨亮解释说,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幸生病了,我们必须住院,摘下饰品,换上病人的衣服,成为三号病房的第五张床。只有服从医生的安排,我们才能尽快出院。这是一个“剥离”自己的过程。
他在之前的论文中描述了一位康复机构“浦和贝塞尔家族”的患者,他加入了日本北海道:他们刚刚离开医院,他们“像羔羊一样温顺,沉默寡言,成为一群失去苦恼能力的人”。 。
该机构最初由四名即将出院的精神障碍患者和一名医疗社会工作者组成。出发点是患者离开病房,想要找到现实生活的感觉,包括重新开始“苦恼”。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去工作。
他们在海边注册成立了一家制造和销售海带的公司,工作相对宽松,符合精神疾病康复者的抗压能力。它已经持续了40年。
“橡子”的精神世界
这家日本公司由三部分组成,销售海带的“贝塞尔有限公司”、同名社会福利法人组织,以及名为“橡子俱乐部”的精神障碍俱乐部。“橡子俱乐部”组织了各种会议,参与者分享了自己的幻听内容和其他症状,以及最近的苦恼和快乐。
“橡子”是精神障碍患者的自嘲:看起来像栗子,但没有栗子的实用价值,不好吃——就像它们对社会没有那么“有用”,很难找到工作,但对自己和朋友还是有价值的。
郭海平的同事李金说,一群不爱社交的精神病人呆在一起,并没有那么亲密,但是他们也会互相关注,想着互相帮助。
有一次,南京原生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带着一群画家出去玩。一个人固执地捡起瓶子,问他,拒绝解释为什么。后来发现他把瓶子给了另一个画家,以为对方家庭条件不好,可以卖钱,怕捡一个给一个,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他们也会有一些小的“竞争”。李金说,有些患者在家吃饭很挑剔:“他(指患者)在家里说了很多次,可能不会接受。但是当你到了恢复的地方,看到别人吃饭简单,画画自然就标准化了。”
身边有一群情况相似的人。李佳鼓励孩子们外出,对他说:“看看别人。他们病得更晚,理论上更难恢复。但是你看到了吗?他们也恢复得很好。”
患者互相照顾,比较生活习惯,恢复水平,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并无相似之处。
“很多人看到这些画很完美,就会想,我们有没有教书,或者帮他们调整一下。”李金说:“但这些人(画家)不会接受外界的干扰。”
在郭海平看来,我们大多数人都在乎社会的评价,而有些病人更在乎自己内心的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更接近某个精神世界的真相。
这个机构展示的一些画与疾病有关。李金给我展示了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作品,都是严格对称的。这种疾病让他非常焦虑,他需要在艺术中找到秩序感。
但是更多的作品并不指向“病”,需要工作室的员工问作者:“这是什么意思?”作者有权解释。
比如牙齿是一个严重的自闭症患者,很早就生病了,没有学到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他努力画画。每次工作人员问他:“这是什么?”他都回答:“窗户,鸟,路。”
在他眼里,这是世界的一角,只有他才能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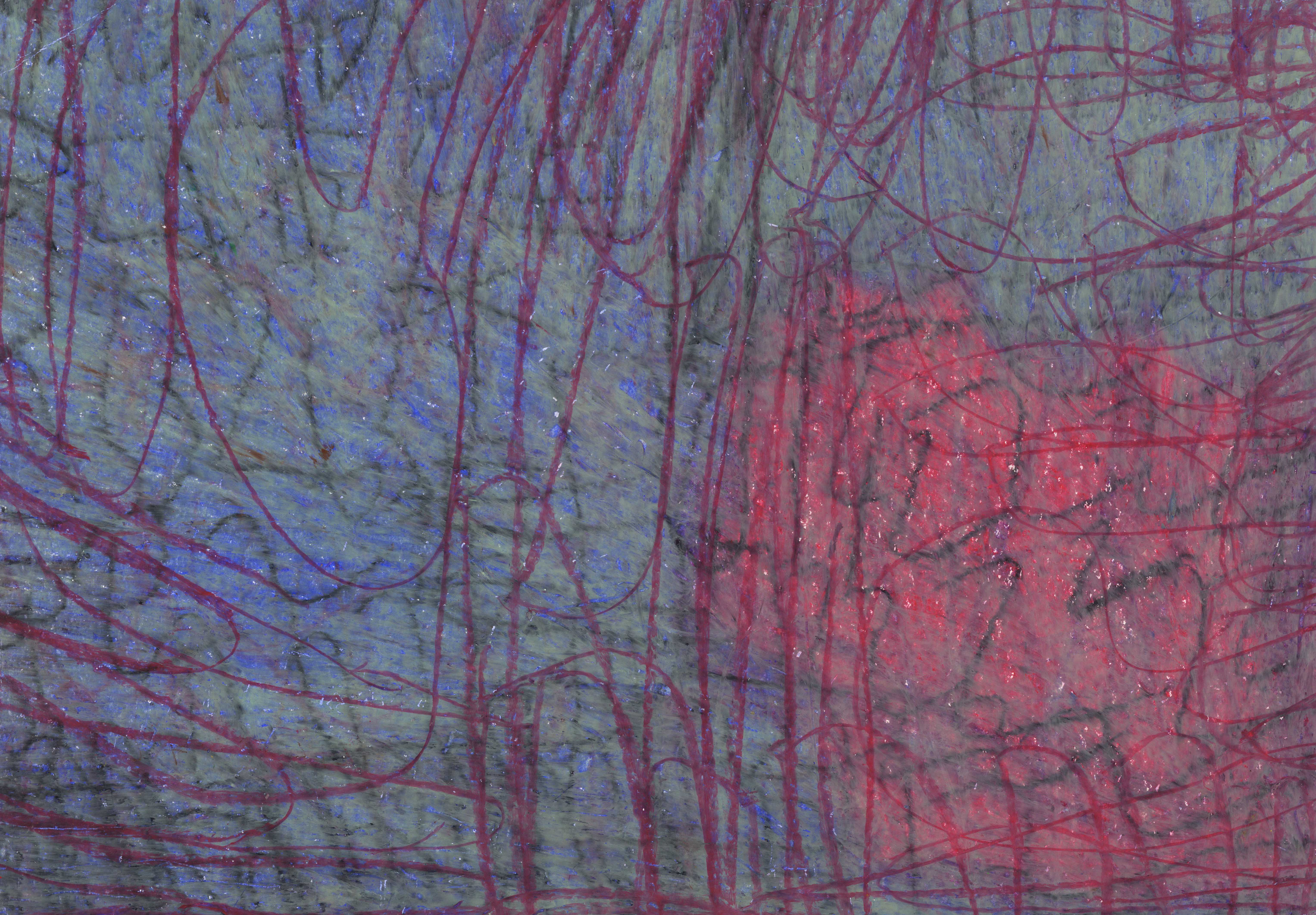
牙齿作品,窗户,鸟儿,道路(一)

牙齿作品,窗户,鸟儿,路(二)
关于一些精神疾病患者和主流社会之间的障碍,杨亮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有幻听的人耳朵里有一个声音,很难再听别人说话了。
病人的幻听有时是一些不好的声音,比如辱骂他,还有一些病例,病人会听到非常有趣的内容。杨亮认识一个病人,用他的幻听作为写小说的素材。
“半途卧室”
郭海平说,他开始这个职业的初衷并非“助残”,而是厌倦了一个严肃的世界。
他问:只有妄想中的精神病人吹牛,普通人不吹牛吗?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谈论事情,有自己的立场。有些话可能听起来比一些说话不调的病人更“假”。
上海市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张英诚解释说,根据动力学的发展观点,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点是“内心融合不好”,不兼容的想法和经历交替出现。“我说我不想活了,但我笑了。”——急性发作的人可能会突然处于这种状态。
如果这种状态好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幻觉和妄想。张英诚说,有些病人似乎生活在孩子的世界里:如果病人说自己是国王,那似乎是不合理的,但我们可以理解,他只是想被关注和喜欢。
他说,不同的病例可能有类似的疾病,但外观背后有不同的动机。比如“思维僵化”可能是神经病理变化直接造成的,也可能与社会因素有关。患者知道自己承受了不认可他的眼光:“为了保护自己,他不得不进入狭隘的思维状态。如果他敞开心扉,外面的东西就会进来。他受不了。”
有些病人的家庭关系是由疾病引起的。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一些欧美国家、中国香港和深圳有一些“半途而废的宿舍”。(halfway house)病情稳定的病人可以借宿。
其中,香港的“半途卧室”由几家不同的社会组织经营,向患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可以由当地的“公共援助”(类似于内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承担。
病人住在这里,比住在病房里自由,能出去打零工,找朋友,重新开始成长。
然而,香港中途宿舍也多次遭到周围居民的困惑,甚至公开抵制。
香港社会福利署工作人员曾出来解释说,刚出院的患者回到社区更容易紧张。如果他们先在宿舍住一段时间,逐渐适应社会,就不容易反复生病。
在南京原生艺术中心,李金告诉我,有些画家会情绪不稳定,但有坡度,“不是突然翻脸”。当她谈到一个画家时,她的同事提前看到他“头晕,说话颠倒”。当他们检查他的状态时,他的脸显得紧张。
“你在工作室,是安全的,”她试图温柔地呼唤他。我是小李老师。大约一个小时后,这波浪也离开了。
能否容忍与大多数人不同的个人,找到共存的方法,考验社会的容忍度。
张英诚说,如果一个人有精神疾病,我们会歧视他,给他贴上污名化的标签。那么,我们也是“僵化的思维”,和我们不喜欢的没有太大区别。
(小鹏,牙齿,何新,李佳是化名。欧阳思帆的见习生也为这篇文章做出了贡献。)

海报设计:白浪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