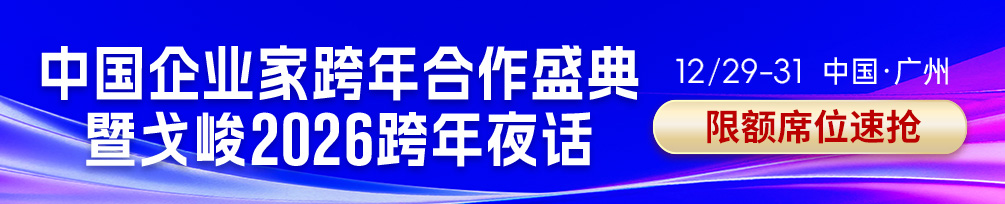汉高祖辱商的目的和困商的逻辑
为什么汉高祖比秦二世更讨厌商人?
贾人没有得到衣锦、绣、绮、竹、竹、竹、竹、竹、竹、竹、竹。
——《汉书·高帝纪下》
尽管传世的《商君书》和《史记·商君列传》都提到了秦国的“重本抑末”政策,秦制的核心逻辑是寻租。,从皇室到老百姓,在所有员工的拜金社会,除了血统高贵、有资格与皇室建立亲密关系的高贵贵族,其余的低贵族、老百姓、徒隶,最大的生存智慧就是通过收敛财富来赎回生存权。商贾市从来不是用户籍标志的“贾人”专利,而是秦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直到秦统一天下。
按照周朝的传统,贵族之间可以进行以礼相待的交换,但要防止自己在贾市买卖,贾市买卖主体应该是贾人。正如《论语·子罕》中子贡和孔子所描述的那样,子贡说,这里有好玉,是不是妥善地收藏在柜子里?或者找个识货商人卖掉好吗?孔子说,卖掉它吧!卖了它吧!我在等商人。这儿有一种歧义,究竟是由子贡把良玉卖给商人,还是子贡把良玉交给商人分销?从“好贾”和“贾”还需要“求”和“待”的意思来看,良玉代表君子之德,而好贾代表君子之德,而好贾代表君子之德,分配代表行道,而不是用能力换取名利。它还是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现实诠释,买卖玉石都要经贾人之手。
简言之,贾市的行为应该由贾人作为中介,贵族应该从贾人那里购买商品,他们支付的货币是黄金而不是铜币,这也是延续到管道时代的一个常见例子。因此,关东六国留下了巨大的“贾人”群体,他们继续管理着“四民分居”的思想。这些人集中生活在城市,户籍与其他类别的人分开。他们需要支付市场租金和税收,但他们享受着普通农民无法企及的“流动”便利,这也是“四民分业”的结果。
春秋之前,贾人以“族”为基准面对政权,地位并不低。然而,战国时期家庭结构的分化也带来了贾人的规模扩张。,一方面在功能上受到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内部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于是出现了千金之富的巨商和“事末利怠而贫” 命运的不同。巨商贾可以和王子一起旅行,而做生意致贫的人会被贬为官奴,就像懒惰致贫的人一样。毕竟巨大的财富是少数,大多数贾人还是要挣扎谋生。
问题在于,秦国的全民经商传统根植于区域分割市场,专职贾人在秦始皇眼中成了“疣疣”。因此,秦朝初年的法律没有考虑到贾人的管理,而是采取了分层迁移策略:富人迁移到咸阳,点缀着国王的房子;富人迁移到巴蜀,开发资源产地;普通贾人被送往岭南,成为边境地区的人力养分。然而,贾人的出现终究是经济的必需品。跨区域物流需要专门的组织。单纯依靠权力转移只会导致各行各业的萧条。因此,秦二世即位后的政策也有所调整。
据岳麓书院藏秦简《金布律》记载,禁止贾人使用高五尺五寸以上的公母马拉车进行交易,或者租用载人、运物、送信。如果他们有命令,他们应该惩罚第二名,没收马。换句话说,在秦二世三年前(207年)之前,秦朝已经认可了贾人的出现,并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由于上述法律与学者和农业行业形成并列关系,特别指出“服车”、“(垦地)田”和“为人就业”。
之所以强调贾人,是因为从“犯令者”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端倪。三十年来,秦始皇(前217年)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管理贾人的律文,仍然借用“魏户律”和“魏奔命律”;到了33年(前214年),秦始皇再次派遣贾人、媳妇、品尝亡人,平定越人叛变,发誓守护岭南。可见秦始皇此时还是想消灭贾人。然而,这场战争在秦二世第一年(前209年)结束,西汉修法是有惯例的。上一代皇帝去世后,新皇帝应该整理和选择先帝的“命令”,并将其纳入“法律”。然后,严禁富贾使用成人健马的“命令”,这很可能是秦始皇末期发布的,秦二世将其纳入金布律。从动机的角度来看,秦二世面临的物资和货币困境也可能驱使他弥补秦始皇的不足,放松贾人待遇应该是其中之一。所以,秦末大乱前后,贾人的宽松环境至少要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开始。
不幸的是,美好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汉高帝8年(前199年)3月发布了一项新法律:“贾人得不到衣服、刺绣、刺绣、刺绣、骑马、骑马。“锦是由不同颜色的丝线编织而成的丝绸织物;它是一种绣有彩色线条和图案的纺织品;它是一种带有线条和丝绸的纺织品;它是由细纱编织而成的皱纹丝绸面料;它是一种带有图案的细葛布;它是一种粗布。是羊毛面料。贾人不能穿上材质的衣服,也不能有武器,不能骑马,不能骑马。在《史记·平准书》中,这一事件被简化为"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与“重租税以辱”并排,看似是同一项政策,也被解读为汉初养生息的重要举措。然而,贾人不得拥有武器或骑马,这显然比秦二世时期的法律更严格。因为秦律显然是为了保护肩膀高达标的好马,而不是专门针对贾人,汉高祖的新政策显然是“辱商”。
随着这项法律的出台,并不是“重租税”,而是“官员们参军到平城,守城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有事情发生”。要知道,平城对决发生在这个指南颁布的前一年,也就是汉高帝七年(前200年)的冬十月。汉高祖在平城逃离了匈奴大军的包围圈,但对参战者的奖励却延迟了这么久,他也“羞辱”了不相关的贾人,这让人联想到因果。
侮辱商人的目的:让商人放下武器
事实上,作为赵代战争的开始,平城对决真的让贾人第一次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在平城对决前夕,被汉军打败的韩王信与下属曼丘臣、王黄共立的赵利为王,外联匈奴为援。他的力量奇迹般地恢复了,甚至引诱了敌人,这让汉高祖陷入了“白登之围”,遭受了自反秦以来最大的屈辱。
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说法,但《史记·匈奴列传》中说,韩王信、王黄、曼丘臣多次违反合同攻击代郡和云中郡,直到镇压陈邈的叛逆,樊邈才再次攻克代郡、雁门、云中县。这意味着雁门郡一直掌握在韩王信残党手中,直到平城对抗陈邈灭亡的四年时间。然后,汉高祖当时对冒顿单于的求和退缩,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承诺,更是一个真正的割地。雁门郡,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代的贸易枢纽,就这样丢了。罪魁祸首是王黄和曼丘臣。根据《史记·韩信卢邈列传》,他们“都是故贾人”。
更有意思的是,在陈邈叛逆的时候,汉高祖拿出一千块钱来欣赏王黄、曼丘臣等人,这让他们在战败后被下属出卖。史书记载显然是为了突出贾人的“重利轻义”,衬托汉高祖对贾人的远见卓识“羞辱”。
问题是,自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冬十月战胜刘邦以来,王黄一直被杀,直到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冬。这些“故贾人”一直割据雁门郡,在赵代之间幸福了四年。唯一的解释是,当“贾人”拿起武器时,他们对王朝的危害远远大于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布等宿将。正是因为汉高祖被“故贾人”打了心理创伤,所以禁止贾人骑马、骑马、拥有武器,以免天下贾人有样学样。
所谓君王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国王的心理阴影自然会影响政治局势,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航向。
汉高帝12年(前195年),汉高祖拖着病体打败了英布。在回长安的路上,他遇到了人们挡路喊冤,指责相国萧何低价买了几千万人民的田宅。看到萧何后,汉高祖把所有的书都给了萧何,让他自己处理。萧何非但没有警觉,反而向刘邦要求开放皇室猎苑上林苑里的空地为百姓耕种。结果是“上大怒”,居然污蔑相国萧何私收贾人财物,才来申请开放皇帝的私苑。一气之下,把萧何打进尉狱,上束缚囚禁。几天后,王卫尉随侍,问起萧何,劝说汉高祖,汉高祖这才释放萧何,萧何赤脚进宫赔罪,汉高祖的话绝对是阴阳怪气,你为人民谋福利,我不许,“我只是为桀纣主,相国是贤相”。所以,我才把你关起来,就是让人们听到我的错误。史书上没有记载萧何如何回应这句话,但汉高祖和王卫尉之间的争论非常有趣。“贾人财物多”、“贾人金多”、“贾人金多”、“贾人金多”的说法经常出现,说明汉初官员和贾人之间的联系到了什么程度,以至于皇帝会相信一个国家会聚在一起,出卖皇家园林作为贿赂。
事实上,在汉高帝十年(前197年),赵相和阳夏侯陈邈叛逆的直接诱因是汉高祖派人查处陈代客人非法牟利的案件。陈先生派门客联系王黄和曼丘臣,因为他们害怕被牵连。可以看出,陈邈客人的生意很大,并且干犯汉代禁令。因此,这些企业的海外合作伙伴很可能是王黄、曼丘臣,才使陈邈能够“客人数千乘,邯郸官舍皆满”。归根结底,养士需要花钱,光是客人就有上千辆车,挤满了七万户大邑邯郸的客房,这笔钱绝非一介侯应有。
粗略地看,汉高祖侮辱商人的政策似乎失败了,降低了商人的地位,使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财富和获得财富的能力,更紧密地与朝鲜的英雄和权贵串通,更疯狂地破坏了“四民分居”的理想公共秩序。但是本质上,汉高祖“辱骂”的,并非“贾人”,而是大大小小的商人挺身而出,实现了东汉商人的理想。说白了,刘邦怕自己的财富变成武器,直接挑战权力秩序。当商人与权贵合作,沉迷于财富本身,甚至产生财富可以赎回权力的错觉时,“羞辱”政策已经有效。当贾人乖乖地放下武器,削尖头脑,适应系统生存时,他注定会错过未来2000年的政治舞台。
困商逻辑:强化产权私有化的“幻觉”
与“辱商”无关的是“困商”,即盘剥商人资产,方法也很简单,就是“重租税”。这里的“租金”不是田租,而是“市租金”,市场交易税。在《二年律》中,要求商家有隐藏交易,不自行申报市场租金。隐藏的市场租金相当于小偷的赃物。商品应该充电,购买的钱应该没收,他们拥有的“市场(摊位和商店)”应该被带走。如果市场上的“伍人”和“列长”没有被揭露,他们将被罚款一公斤。、负责人(官员)没有发现,要罚两两。可以看出,市列的管理包括市里的年轻人、官员、列长、伍人,形成连坐关系,类似于村里的年轻人、官员、里正、伍老的管理序列。市列组织也是典型的编户齐民结构,通过“自占”、“强奸”、“连坐”来管理。
秦汉有交易必须在“城市”,同行业在同一个市场的规定。岳麓书院秦简《为监狱等四种情况》中的《瑞盗出售公共土地案》说明,秦时的“市列地”和农田一样,都是“接受”的,采用国有土地申请制度。同一个家庭在“受列”之后,不能拥有同一个行业的列地,可以转赠,可以出售,但是需要市曹定价和登记。也就是说,“市肆”、“舍客室”等经营性产业,只要在“列地”上,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还要缴纳“地租”。
因此,在市场上,根据市民考试课程,无论经营者是否具有贾人身份,市场交易税都可以归纳为“市场租金”,官员可以设定“市场课程”(税收指标)。西汉后期大臣何武有个小弟叫何显,在老家蜀郡当郡官,“显家有市籍,租不入,县数负其课”。可以看出,到了西汉后半段,市租仍然有政府规定的“课程”指标。因此,在西汉初期,商人的“重租税”,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市课”来实现。
离任前,时任齐相国的曹参对接任者说:“以齐狱市为寄,谨慎不打扰。”“接任者不明白,治国难道没有什么比诉讼和市场更重要的了吗?曹参的解释是黄老之风。刑狱和市场是“兼容”的关系。刑狱是苛刻的。破产者和剩余的人最终会去市场谋生,聚集更多的人会制造混乱。政府干预市场太多,浮食者没有生计,会非法作乱。因此,“扰乱”监狱和城市的结果是社会动荡。
说白了,曹参的政策就是承认“奸人”的出现,以暴利的商业行为将其容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在这种环境下,“重租税”不是“干扰”,而是汉朝给私有财产所有者的定心丸。由法律法规背书的有据可依的重税,可以让贾人感受到久违的秩序感,强化私有产权的幻觉,进入恒产者有毅力的稳定状态。
秦汉的税收逻辑不同于今天的税收逻辑。“租”和“税”是根据不同的产品定义的。学术界公认的解释是,实物税是“租”,货币税是“税”,但实践中“租”和“税”的区别并没有严格定义。“租”税目中也会出现“税”字样,实际上标注了分为征收或货币化征收的规则。更深入地说,“租赁”的思想在于收益的可预测性,而“税收”的思想在于收益的不可预测性。
秦代商业税记载为“关市之赋”。张家山汉简的《算数书》也有记载,带货通过副本,需要支付过路费,又称“租”,可见, “关租”与“市租”的结合就是“关市之赋”。然而,秦朝的商业行为不仅仅是这个负担,还有一种叫做“()税”的财产税。作为秦朝这种税收存在的重要依据,岳麓书院秦简《为狱等四种情况》中收录的“识劫案”明确提到了“(通)税”和“占家”。在官员的“)”中,他们指出“匿税(值)超过660元”,但“匿税”和“布肆”。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的案卷并未提及“匿税”案当事人是否为贾人,是否为市籍。如前所述,商鞅变法后,秦国全体员工经商。“税收”的征收范围不仅限于贾人,而且面向全民。关键因素是商业行为。简而言之,秦朝的“税收”是以营业收入的不可预测性为基础,以有商业经营行为的家庭货币资产为征收对象的税种,一般来说,对于“资本”纳税,对其它“资产”不征税。
作家:刘三解
出版社:北京科技出版社
制作方:Mark记号
标题: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
摘自《黄铜资本:帝国中国经济的源代码》。作者:经北京科技出版社授权,刘三解转载虎嗅。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