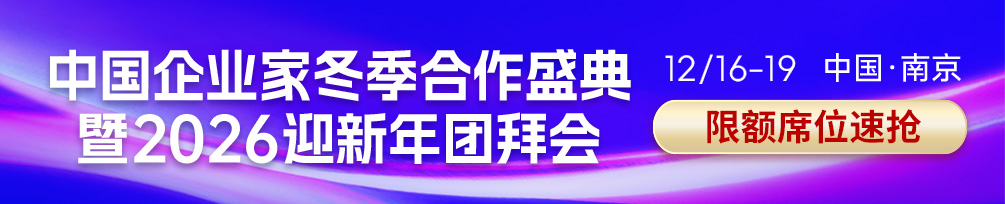陈天桥:管理学的黄昏与智能的黎明——重塑企业的生物学基因


盛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创始人
陈天桥
引言:
管理学的黄昏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言,动荡时代最大的危险并非动荡本身,而是沿用昨日的逻辑行事。
如今,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危险的临界点。
从系统演化视角来看,管理学并非永恒真理,这并非因其理论存在缺陷,而是其服务对象——碳基生物的大脑即将被智能体替代,管理学存在的前提也将被物理性移除。
因此,未来企业变革并非基于AI的“更优管理”,而是“管理的退场”。这无关对错,而是结构的必然。当执行不再依赖生物特征时,基于生物特征构建的制度大厦,其历史使命便已终结。
第一章:
历史的代偿——管理即“纠偏系统”
现代管理学的大厦,实则建立在“生物局限性”这片沼泽之上。过去百年间,我们推崇的所有管理工具,本质上都是为人类大脑打的“补丁”:
我们发明KPI,并非因其能精准衡量价值,而是人类大脑难以在长周期中锁定目标,“遗忘”是碳基生物的常态,我们需要路标指引;
我们发明科层制(Hierarchy),并非因其高效,而是人类工作记忆仅能处理7±2个节点,为避免认知超负荷,被迫通过层级压缩信息;
我们发明激励机制,并非为创造价值,而是为对抗生物体天然的动机衰减与熵增。
管理学从未真正提升组织的“智能”。它是一套精密的“纠偏系统”,试图在人类心智失效前,用制度锁定正确性。
当执行依赖人类时,企业便是为适配大脑缺陷而构建的制度容器。
第二章:
智能体的介入——全新的“认知解剖学”
那么,我们要引入的替代者究竟是什么?
请注意,当我说“智能体(Agent)”时,并非指运行速度更快的软件,而是一种在认知解剖学(Cognitive Anatomy)上与人类截然不同的存在。
若将人类员工与智能体放在解剖台上对比,会发现三处根本性生理差异:
第一,记忆的连续性。
人类记忆瞬时且易碎,依赖睡眠重置,上下文常断裂。而智能体拥有EverMem(永恒记忆),并非片段工作流,而是连续历史。它不会遗忘,无需“交接”,每一次推理都建立在全量历史的基础上。
第二,认知的全息性。
人类受带宽限制,必须通过层级过滤信息。而智能体具备全量对齐(Context Alignment)能力,无需通过部门周会同步信息,整个组织的知识网络对它实时透明。它看到的是全局,而非盲人摸象般的局部。
第三,进化的内生性。
人类动力依赖多巴胺和外部奖赏,易衰减。而智能体的行动源于奖励模型(Reward Model)的结构张力。它无需被“哄”着工作,每一次行动都是为让目标函数收敛。
这不是更强的员工,而是基于不同物理法则运转的新物种。
第三章:
基石的崩塌——新物种遭遇旧容器
如今,当我们将这种具备“连续记忆、全息认知、内生进化”的新物种,强行塞进为人类设计的旧管理容器时,会发生什么?
系统性排异反应开始显现。那些曾支撑现代企业的五大基石,正从“必要保障”异化为“智能束缚”:
KPI的崩塌:从“导航”变为“天花板”
我们需要KPI,原是因人类易迷路。但对时刻锁定目标函数的智能体而言,死板的KPI指标反而限制了它在无限解空间中寻找更优路径的可能。这就像给自动驾驶汽车画死轨道,却期待它躲避突发障碍。
层级结构的崩塌:从“过滤器”变为“阻断器”
我们需要层级,原是因人类大脑处理不了过多信息。但对能处理千级上下文的智能体来说,层级结构不再是过滤器,而成了阻碍数据自由流动的“血栓”。在智能网络中,任何中间层都是对信息的无谓损耗。
激励机制的崩塌:从“动力源”变为“噪音”
用外在激励驱动智能体,如同用糖果奖励万有引力,无效且滑稽。它不需要多巴胺,需要的是精准的数据反馈。
长期规划的崩塌:从“地图”变为“模拟”
我们需要五年规划,是因无法在高频变化中维持长周期推演。但在智能体手中,静态战略地图被实时的世界模型模拟(World Model Simulation)取代。既然每秒能推演一万次未来可能性,为何还要死守半年前打印的旧地图?
流程与监督的崩塌:从“纠偏”变为“冗余”
传统监督机制原是为盯着人不犯错。但在智能体内部,理解即执行,感知即行动。监督不再基于对执行过程的怀疑,而是基于对目标定义的再校准。
第四章:
终极形态——AI-Native企业的五项根性定义
若抛弃这些生物学拐杖,真正的AI-Native企业,其终极形态究竟是怎样的?
这不再关乎企业应购买何种软件,而是企业应以何种生物学形式存在。真正的AI-Native企业,必须在基因层面完成以下五项重塑:
1. 架构即智能(Architecture as Intelligence)
传统企业架构是社会学产物,旨在解决人际摩擦。而AI-Native架构是计算机科学产物。
整个组织本质上是一个庞大的分布式计算图(Computational Graph)。部门不再是权力领地,而是特定功能的模型节点;汇报线不再是行政命令通道,而是高维数据流转的总线。企业架构的设计目标,从“管控风险”转变为“最大化数据吞吐与智能涌现”。
2. 增长即复利(Growth as Compounding)
传统增长依赖线性人力堆叠,边际成本随规模递增。AI-Native增长依赖认知复利。
智能体的核心特征是“零边际学习成本”。一次成功的边缘案例处理,其实验结果会瞬间同步给全网智能体。企业估值逻辑将彻底改变——不再取决于员工数量规模,而是取决于认知结构复利的速度(Rate of Cognitive Compounding)。
3. 记忆即演化(Memory as Evolution)
无记忆的智能只是算法,有记忆的智能才是物种。
传统企业的记忆是离散且易碎的“死数据”。AI-Native企业必须拥有可读写、可进化的长期记忆中枢(Long-term Memory)。所有决策逻辑、交互历史与隐性知识,都被实时向量化,沉淀为组织的“潜意识”。这是企业实现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的基础,也是智能跨越时间自我演化的前提。
4. 执行即训练(Execution as Training)
在旧范式中,执行是消耗过程,价值交付即终点。在AI-Native范式中,执行是探索过程。
不存在单纯的“执行部门”,所有部门本质上都是“模型训练部门”。每一次业务交互,都是对企业内部“世界模型”的一次贝叶斯更新(Bayesian Update)。业务流即训练流,行动即学习。
5. 人即意义(Human as Meaning)
这是企业伦理的重构。人类从“燃料”角色中退出,升维为“意图策展人(Intent Curator)”与“认知架构师(Cognitive Architect)”。
智能体负责在无限解空间中解决“如何做(How)”的问题,进行路径极值优化;而人类负责处理那些不可计算的模糊性——定义“为何做(Why)”,定义审美、伦理与方向的价值函数(Reward Function)。智能负责拓展可能性边界,人类负责裁定方向的意义。
结语:
智能的黎明
这与我们在科学领域提出的发现式智能(Discoverative Intelligence)殊途同归。
发现式智能的核心定义是:智能不应止于对既有知识的拟合,而应具备构建模型、提出假设、并在与世界交互中修正认知的能力。
AI-Native企业,正是发现式思维在组织层面的投射。它要求企业本身成为发现式结构的平台,而非操作流程的容器。
若组织形式正在发生物种级演化,那么承载它的数字容器也必须随之突变。
这引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命题:我们脚下的基础设施——那些为固化流程而生的ERP,那些为切割职能而建的SaaS——真的还能容纳这种液态智能吗?这些系统本质上是旧时代管理逻辑的数字化投影,通过“打补丁”或许能带来暂时安宁,但终究是用旧地图寻找新大陆。
AI-Native企业呼唤一种全新的操作系统。一种不再致力于“资源规划(Resource Planning)”,而是致力于“认知演化(Cognitive Evolution)”的全新神经系统。
当管理退场,认知升起。
管理学不会消失,但它将首次真正建立在智能(Intelligence)的地基之上,而非生物学(Biology)的废墟之上。
未来的企业,不再是人领导智能,而是智能扩展人。
陈天桥 | 文
陈天桥是盛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创始人
*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哈佛商业评论立场
联系方式
投稿、广告、内容和商务合作
newmedia@hbrchina.org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