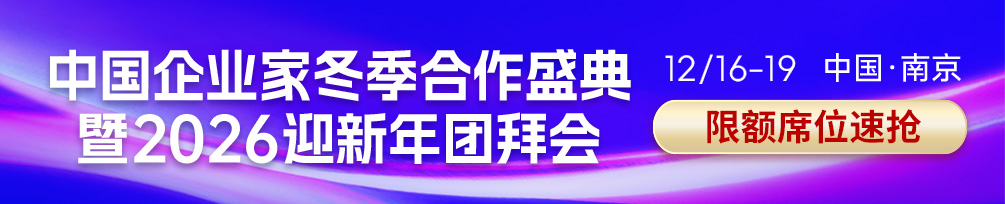带着谦卑却不自卑的姿态——《我的故乡》的中国初印象
“我叫根纳,来自白俄罗斯……”腼腆的男主角用略显生硬的英语,为《我的故乡》在上海的首演拉开了序幕。戏中水管工根纳短暂离开明斯克前往伦敦的情节,恰似现实中白俄罗斯戏剧踏上中国之旅的写照。
在《我的故乡》演出间隙,白俄罗斯剧作家阿纳斯塔西娅·瓦西列维奇来到杨浦区图书馆,以“白俄罗斯戏剧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为题展开演讲。她开篇便展示了一张东欧地图,帮助本地观众清晰了解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它东邻俄罗斯,被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环绕。白俄罗斯共和国戏剧院院长斯维特兰娜·瑙缅科透露,该剧院自1990年成立以来,在此次上海YOUNG剧场演出前,唯一一次中国之行是11年前受北京人艺邀请参加首都剧场剧目展演。对于这里的观众而言,白俄罗斯及其戏剧都还十分陌生。

《我的故乡》开场时,无论是戏的内容还是演员的状态,都显得十分谦逊。戏里的男主角和戏外的白俄罗斯戏剧,都在小心翼翼地向这个陌生的世界“介绍自己”。看完这部90分钟的作品,虽然它尚不足以定义“白俄罗斯戏剧”这一宽泛的概念,但这群年轻演员的表演以及作品内在“谦卑却不自卑”的气质,却格外动人。《我的故乡》由白俄罗斯戏剧创作中心的青年编剧和演员集体创作而成,这支团队在欧洲乃至国际戏剧舞台上几乎“默默无闻”,但他们在剧场中展现出的戏剧格调,值得更多青年创作者深思。
这里所说的戏剧格调,首先体现在内容上的“谦卑不自卑”。《我的故乡》让人们看到,有这样一群年轻人愿意用戏剧的形式,讲述那些微不足道的人和事。小人物无需被拔高、被升华,并非只有成为“平凡生活的英雄”才有被看见的资格。
根纳是明斯克近郊乡镇的一名水管工,年纪轻轻便稀里糊涂地结了婚,糟糕的婚姻破裂后,他一度浑浑噩噩,还因偷窃被判入狱一年半。提前出狱后,他重新干起水管工的活儿,却并非洗心革面的模范工人,对脏活累活颇有怨言。他就是那种辛苦生活却泯然众人的“普通人”,这样的主角在商业剧场或先锋实验戏剧中并不常见。根纳人生的高光时刻,来自他的业余爱好——草编。他的作品入围了某个欧洲手工艺品赛事的决赛,因此受邀前往伦敦参加颁奖礼。主角光环终于降临到根纳身上!他能否凭借出色的草编手艺在英国成为一名艺术家?当他偶然看到伦敦管道工人先进的操作设备时,能否依靠在家乡落后条件下磨练出的技能,在更好的工作环境中成为抢手的技术工?答案都是否定的。到伦敦的第二天,他就疯狂地想要回家,五天后便坐上了返程的航班。当飞机进入白俄罗斯领空时,他泣不成声。根纳很有自知之明地分析,自己对家乡的强烈羁绊并非源于“爱国主义”,而更可能是常被“城里人”和“全球化世界主义者”嘲笑的“小农的乡愿”。
为何有手艺、有技能的年轻人宁愿被家乡牵绊,也不愿去远方闯荡?这个问题本可以催生出一部更具思考性或批判性的戏剧。但《我的故乡》的创作者们,却选择将目光投向那些被忽略的人和情感,让那些“不上台面”的人和事成为戏剧的主角。这或许不是对深刻的追求,却留住了当代戏剧中正在消逝的温情。

《我的故乡》的戏剧格调还体现在表达形式上的“谦卑不自卑”。现任院长斯维特兰娜·瑙缅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梅耶荷德的创作方法论,剧作家阿纳斯塔西娅·瓦西列维奇在德国留学期间,常去邵宾纳剧院观看演出,德语戏剧是她的研究课题之一。因此,对欧洲戏剧传统与现实的广泛吸收和学习,在剧院年轻人的集体创作中得以体现。
《我的故乡》的剧作文本采用根纳的主观视角进行独白,台上的表演者包括男主角和一群女演员。当根纳面对观众陈述时,麦克风上绑着即时摄像设备,他的表演特写会投影在舞台后方的银幕上,这一手法明显借鉴了近20年来邵宾纳剧院和柏林人民剧院的常用思路。女演员的群戏以歌唱和舞蹈穿插在根纳的独白中,合唱既包含根纳内心的秘密,也有对他行为的评述,这其实与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类似;群舞编排是对歌队的视觉补充,既灵活运用了梅耶荷德的理论,又巧妙借鉴了当代欧洲的肢体剧场。整场表演让观众看到,这群青年演员眼界开阔且有明确的方向,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创作方法在同一个舞台上并未显得生硬拼接,而是形成了“我们的表达”。学习“传统的”“世界的”“他人的”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我们的”,这不仅不是自卑的表现,更是一种自信的创作审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