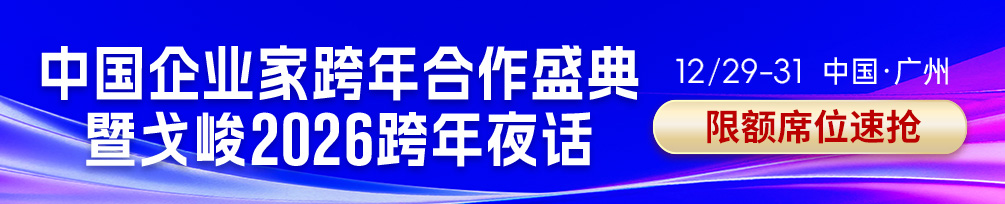双面《戏台》:老祖宗与旧时代的多面映射
余少群在《戏台》中扮演凤小桐

“戏台”充满神秘色彩。前面是观众席,一排排座位延伸开去,看似很近实则遥远。后面是后台,连接着出将入相的门,通向化妆间和演员通道。有演出时,在灯光照耀下,尽管大家都知道台上演的是“假”故事,但总会投入“真”情感。如此,“戏台”超越了实体建筑的内涵,成为某种“意象”。
一
陈佩斯对“戏台”情有独钟,《戏台》和《惊梦》都是如此。戏台两边,不同的强势力量相互博弈,使得戏台变得歪歪扭扭、支离破碎。
电影《戏台》开篇就是军阀混战,枪炮声不断,电影还特意给了大炮巨大特写,炮弹气场十足。在情节推进中,大帅乔装闯入“戏台”,一开始被当成“三花脸”,可当他掏出手枪,给“强势”的精神大佬八爷开了个窟窿眼时,他就成了“戏台”上下绝对的强权代表。
当枪炮介入戏剧,戏剧就变得脆弱了,这不是戏剧人能左右的。凤小桐再不愿意,也得忍着恶心给洪大帅唱唐山落子味的《别姬》。相比意味更隽永的《惊梦》,我更认可《戏台》的真实。在《惊梦》中,举着枪的士兵被高雅精致的《惊梦》艺术折服而不开枪,这太“浪漫”了。枪炮不会被艺术的“美”折服,反而因能操控艺术存亡而更显残酷。所以,《戏台》结尾,面对真霸王演出的《霸王别姬》,枪炮齐飞更真实,它反映出旧时代权力傲慢的本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二
陈佩斯内心充满矛盾。他知道戏剧脆弱,却也深知戏剧之美。在《戏台》结尾,一边是枪炮轰鸣,戏台摇摇欲坠,另一边,惊魂未定的戏迷们却在《霸王别姬》的绕梁之音中沉醉。此时,或许陈佩斯自己都没意识到,《戏台》中的戏剧/艺术有了另一种内涵:鸦片。
《戏台》中的鸦片形成了闭环。从金啸天吸麻大烟出场,到人们沉醉于战火中的《霸王别姬》,作品从吸鸦片开始,又以吸鸦片结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旧时代艺人的生存处境:乱世中,人命如蝼蚁,不妨麻醉自己和别人。
这种麻醉不仅体现在情节叙事的首尾呼应上,六姨太是中了戏剧/艺术麻醉的典型代表。她是金啸天的戏迷,爱屋及乌,爱金啸天的戏、人以及霸王扮相,不惜以身相许、盲目“私奔”。六姨太展现出“非理性”特征,成了作品中明显的性魅符号。她可以献身大帅、金啸天,甚至“假霸王”大嗓儿,看任何名伶都迷醉其中。尽管这一人物设定有刻板印象,但也让作品中的名伶和名剧有了鸦片的质感。它有诱惑力,却不能改变糟烂社会中人的处境。
如梦似幻的六姨太给了大嗓儿梦幻般的体验。他一直觉得自己在做梦,当被哄着扮霸王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像做梦;六姨太出现又消失,他也以为是做梦。这种体验就像吸鸦片。对于大嗓儿这样的苦命打工人,“戏”是乱世中唯一的超物质体验和精神寄托,就像被困垓下的楚霸王听到四面楚歌无可奈何,只能跟唱聊以自慰。这也能解释传统老戏里为何有糟粕内容和自我催眠的元素,身逢乱世,草民无奈又可怜。
三
与其他艺术样式不同,戏剧很难个人创作。演职人员是群体,涉及各部门,观众也是群体,没有观众现场参与,戏剧就不成立。所以,戏剧天然具有公共性,创作过程包含复杂因素,最终往往是互相理解和妥协。
在中国戏剧历史上,这种妥协很常见。比如优孟衣冠,演员用调笑方式向楚王表达对孙叔敖后人的关切,楚王明理,让“妥协”成了美谈。但清朝王室贵胄喜爱京剧,京剧艺人却如履薄冰,奉诏时为让主子看得舒服,头天晚上扮好不敢卧床而睡,可见其小心谨慎。
在中国戏剧真实历史和个体演艺阅历中,旧时代艺人的处境显现出来:在傲慢的绝对权力面前,文艺或许可爱,但文艺人未必受尊重。当文艺人不受尊重甚至不再自尊时,文艺就变得不可爱甚至面目丑陋。对于戏/艺来说,这就像进入“乱纪元”,乱世中,戏如人,都在苟且。戏台之“兴”背后,隐藏着家国之“亡”,值得深思。
四
陈佩斯认为喜剧是一种结构,电影《戏台》结构繁复。但观众认可《戏台》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讥刺世事和忧愤感怀,而非仅喜剧结构。在“信息不对称”上,人物过多,前后设定难统一,精细度不够,结构显得繁琐。是否有必要增加那么多小零件,把榫卯零件换成简洁建筑材料是否更具现代感,观众其实很包容。
无论是话剧还是电影,《戏台》都强调对“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的认可,这值得斟酌。传统有底蕴,但也有杂质,如鸦片、封建、等级秩序等。“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里可能包含阴暗与腐朽。陈佩斯过于强调“老祖宗”的神圣,无意美化了旧时代,如剧中美化偷情、睡粉、吸鸦片,使作品有了麻醉般的幻梦感,这是不足之处。
(方冠男 作者为云南艺术学院副教授,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