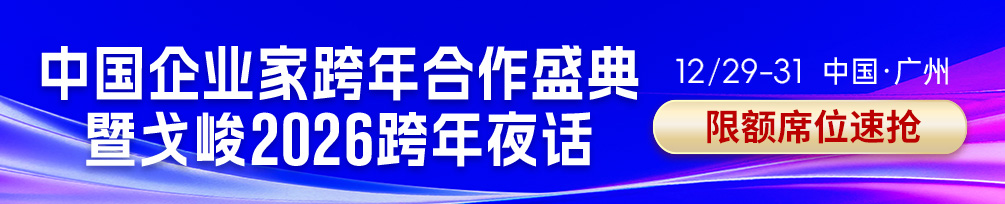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是佩尔主演的经典《樱桃园》。

经典的《樱桃园》由于佩尔主演。
从现实主义的传统解读到风格多样的现代解读,契邈夫内容的排练对中国观众来说并不陌生。在世界各地,为了完成对戏剧传统规则的超越,各国导演都将其视为美学的试金石。蒂戈·罗德里格斯导演、伊莎贝拉·于佩尔主演的《樱桃园》最近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也是创作者借助经典自我挑战的尝试。
悲欢复调里 精致的于佩尔失焦
从1902年到1903年,契邈夫创作了人生中最后一部戏剧《樱桃园》。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前一年,契邈夫站在世纪的悬崖边上,经历了俄国最动荡的激变阶段。这部剧中社会阶层的流动和新旧思想的分歧都来自于此。然而,契邈夫的戏剧通常故意淡化表面矛盾,将视角聚焦在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是在反映人类共同的内心世界。
当代排练的《樱桃园》数不胜数,创作者首先要了解契邈夫的本意,在此基础上引申出自己的解读。在原著中,柳鲍芙等人无法挽回现实的艰辛和美好事物的消失,仿佛笼罩在悲伤和忧郁的情调中,但契邈夫将《樱桃园》定义为“喜剧”。1904年,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第一次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排练这部剧时,他把它解释为一个沉重的抒情不幸,这引起了契邈夫的不满。他称之为“愚蠢的悲伤主义”。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彼得·布鲁克、林兆等的排练都注入了这部电视剧的内在喜剧。
同样,导演罗德里格斯也没有简单地将《樱桃园》解读为一首告别和结束的悲歌。他敏锐地捕捉到契邈夫的怜悯和隐患,试图创造一个悲伤的复调,讨论时代的变化、痛苦和希望并存。
那么,这种悲喜交加的内涵从何而来?这一版本中,柳鲍芙被塑造成了一个“喜剧中的悲伤角色”。她不愿意积极接受现实的改变,一味地沉迷于怀旧的忧郁。除了老佣人费尔斯,其他角色隐约注意到未来与过去大不相同,寻找希望的微芒,奔向未来的新世界,与柳鲍芙的逃避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扮演柳鲍芙的于佩尔以一种疏远的态度走过人群。她没有太多的情绪外化,以醉醺醺的状态观望一切——当我们聚在一起狂欢时,她低下头,独自坐在樱桃树下,周围的噪音与她无关,仿佛她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表演风格越来越凸显了人物与时代的分离感,柳鲍芙所做的一切反应也随之蒙上了荒诞的色彩。
2001年,在戏剧《美狄亚》中,于佩尔极具张力的“尖叫”表演令人印象深刻。不同的是,她在《樱桃园》中演绎的柳鲍芙更加细腻,在迷茫与清醒、幼稚与成熟、温柔与躁动之间不断摇摆。对于人物复杂心中静水深流的刻画,正是在电影中,佩尔最擅长的。但是,没有镜头的焦点和放大,这种表演在戏剧舞蹈&上很难被观众注意和看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观众带着对佩尔的期望进入剧院,却失望而归。
情境转换後 具体指涉失效
本版《樱桃园》作为2021年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开幕剧,承载着当代欧洲的社会问题。法国观众应该能够更好地解读选人的意图——商人罗巴辛和柳鲍芙的下一代安尼雅和瓦里雅,他们的演员不是法国演员,而这些角色恰恰属于剧中的“新世界”。在“樱桃园”逝去的时候,无论是租来的地方,还是为别人打工,他们都有自己的去向。然而,对于以柳鲍芙和老费尔斯为代表的停滞在旧时代的人来说,这些“新世界”的作用就是打破日常生活的“外来者”。
此外,这部剧的创作背景和首演时间也是打破其主题的关键。这部剧创作的时候,法国很多曲目都不能如期上演,整个社会都面临着强烈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必须进入一个重构的新世界,就像剧中的角色一样。
但是,当台下的文化语境发生变化时,这部剧的意义一定会被削弱,外国观众很难带入自己的生活体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未知的距离感。这种现象也印证了一个道理:戏剧艺术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而存在。
从阿维尼翁教皇宫首演的露天广场,到国家大剧院的室内镜框舞&,表演空间的变化也使得观看和表演的关系偏离了导演的创作初衷,虽然导演加入了打破这场中国表演的“第四堵墙”。、与观众拉近距离的设计:罗巴辛一上来就用中文与观众打招呼;表演期间,管家叶比多霍夫邀请观众一起吟诵表达爱意的歌谣;当疯狂的声音停止时,罗巴辛又跳了出来:“契邈夫本可以在这里停下来,但他写了第四幕。"这些互动吸引了观众不断的笑声。“这些互动吸引了观众的笑声。另外,整部剧的演员很少上下场,整个过程基本没有变化的灯光平等照亮每一个角色,甚至观众台也比普通表演更亮。可见导演为了达到间隔效果付出了很多努力,但由于镜框舞&固有的“神圣感”和观剧礼仪的限制,观众对户外环境失去了自由感,略显僵硬。
现代诠释中 角色之间的关系是无序的
无论是视觉上还是听觉上,这个版本的《樱桃园》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就是“现代”。在19世纪末的俄国庄园里,舞蹈设计没有图解原剧中的物理空间,进而构建了一个源于剧本却极其简单的写意空间。随着表演的不断移动、排列和组合,三个弯曲成树形的华丽灯架,三个笔直的铁轨,以及从整齐到凌乱的椅子。一直在场的摇滚乐队源于剧本中反复提到的“犹太乐队”。叙事节奏在音乐中起伏不定,幕间传来的歌曲也将人物难以形容的内在外化。第一幕开始,柳鲍芙回到庄园后,演员们唱了同样的歌词,但每个人的处理都不一样——罗巴辛停止了说话,柳鲍芙假装开心。非现实的场景让人物从遥远的特定时空中抽离出来,进入特定的矛盾,让观众觉得这样的故事还在重演,他们也在其中。
《樱桃园》可以称之为一部群像剧,似乎与对方无关的事件交织在一起。导演罗德里格斯增强了这种失序感,让他活在当代人的生存中。在他看来,每一个角色都应该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他们的和声形成了这个复调戏。在整部剧中,最明显的改编是杜尼亚莎、雅沙和叶比多霍夫这组经常被忽视的情感关系。起初,杜尼亚莎激动地反复告诉大家,叶比多霍夫向她求婚!可没过多久,跟随主人从巴黎回家的雅沙就用花言巧语俘获了她的心。三个人之间没有狗血的矛盾,联系的暗流都隐藏在语言之下。当比多霍夫起曼陀林向杜尼莎求助时,她和雅沙跳舞,两人越来越近...此时此刻,慵懒奔放的法国感情展现出来。
他的作品中的人物让我们感到亲近,这就是契邈夫之所以让人感到亲近。她们的爱,她们的痛苦,她们的喜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我们是当代人。"(摘自伊利亚·爱伦堡的《重读契邈夫》)纵观整部剧,最现代的角色是夏洛蒂莫。她有一段自我报告的独白:“我没有人可以谈论它。我总是孤单,孤单,没有亲戚朋友。我是谁?为什么我还活着?我甚至不知道……”100多年前,契邈夫利用这位女家庭教师的口中,天才似乎说出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孤独而荒谬地寻找存在的价值,质疑存在的虚荣心。
在这个版本的《樱桃园》中,夏洛蒂穿着鲜艳的红色连衣裙,在昏暗的舞蹈&基调上极其显眼,但她总是一个人在事件之外,似乎被刻意削弱了,但导演给她增加了一部原剧本中没有的剧——她向老管家费尔斯坦白。新与旧,年轻与衰老,荒谬或独特...导演给观众留下了解读的空间。
正如罗德里格斯在导演的解释中所说:“樱桃园是关于一个尚未完全理解的新世界的痛苦和希望。”通过这部剧,契邈夫告诉大家,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沉沦悲观,而是要大声喊“你好,新生活!”(朱彦凝)
拍摄/Christophe Raynaud de Lage Festival d’Avignon

经典的《樱桃园》由于佩尔主演。
从现实主义的传统解读到风格多样的现代解读,契邈夫内容的排练对中国观众来说并不陌生。在世界各地,为了完成对戏剧传统规则的超越,各国导演都将其视为美学的试金石。蒂戈·罗德里格斯导演、伊莎贝拉·于佩尔主演的《樱桃园》最近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也是创作者借助经典自我挑战的尝试。
悲欢复调里 精致的于佩尔失焦
从1902年到1903年,契邈夫创作了人生中最后一部戏剧《樱桃园》。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前一年,契邈夫站在世纪的悬崖边上,经历了俄国最动荡的激变阶段。这部剧中社会阶层的流动和新旧思想的分歧都来自于此。然而,契邈夫的戏剧通常故意淡化表面矛盾,将视角聚焦在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是在反映人类共同的内心世界。
当代排练的《樱桃园》数不胜数,创作者首先要了解契邈夫的本意,在此基础上引申出自己的解读。在原著中,柳鲍芙等人无法挽回现实的艰辛和美好事物的消失,仿佛笼罩在悲伤和忧郁的情调中,但契邈夫将《樱桃园》定义为“喜剧”。1904年,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第一次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排练这部剧时,他把它解释为一个沉重的抒情不幸,这引起了契邈夫的不满。他称之为“愚蠢的悲伤主义”。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彼得·布鲁克、林兆等的排练都注入了这部电视剧的内在喜剧。
同样,导演罗德里格斯也没有简单地将《樱桃园》解读为一首告别和结束的悲歌。他敏锐地捕捉到契邈夫的怜悯和隐患,试图创造一个悲伤的复调,讨论时代的变化、痛苦和希望并存。
那么,这种悲喜交加的内涵从何而来?这一版本中,柳鲍芙被塑造成了一个“喜剧中的悲伤角色”。她不愿意积极接受现实的改变,一味地沉迷于怀旧的忧郁。除了老佣人费尔斯,其他角色隐约注意到未来与过去大不相同,寻找希望的微芒,奔向未来的新世界,与柳鲍芙的逃避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扮演柳鲍芙的于佩尔以一种疏远的态度走过人群。她没有太多的情绪外化,以醉醺醺的状态观望一切——当我们聚在一起狂欢时,她低下头,独自坐在樱桃树下,周围的噪音与她无关,仿佛她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表演风格越来越凸显了人物与时代的分离感,柳鲍芙所做的一切反应也随之蒙上了荒诞的色彩。
2001年,在戏剧《美狄亚》中,于佩尔极具张力的“尖叫”表演令人印象深刻。不同的是,她在《樱桃园》中演绎的柳鲍芙更加细腻,在迷茫与清醒、幼稚与成熟、温柔与躁动之间不断摇摆。对于人物复杂心中静水深流的刻画,正是在电影中,佩尔最擅长的。但是,没有镜头的焦点和放大,这种表演在戏剧舞蹈&上很难被观众注意和看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观众带着对佩尔的期望进入剧院,却失望而归。
情境转换後 具体指涉失效
本版《樱桃园》作为2021年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开幕剧,承载着当代欧洲的社会问题。法国观众应该能够更好地解读选人的意图——商人罗巴辛和柳鲍芙的下一代安尼雅和瓦里雅,他们的演员不是法国演员,而这些角色恰恰属于剧中的“新世界”。在“樱桃园”逝去的时候,无论是租来的地方,还是为别人打工,他们都有自己的去向。然而,对于以柳鲍芙和老费尔斯为代表的停滞在旧时代的人来说,这些“新世界”的作用就是打破日常生活的“外来者”。
此外,这部剧的创作背景和首演时间也是打破其主题的关键。这部剧创作的时候,法国很多曲目都不能如期上演,整个社会都面临着强烈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必须进入一个重构的新世界,就像剧中的角色一样。
但是,当台下的文化语境发生变化时,这部剧的意义一定会被削弱,外国观众很难带入自己的生活体验,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未知的距离感。这种现象也印证了一个道理:戏剧艺术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而存在。
从阿维尼翁教皇宫首演的露天广场,到国家大剧院的室内镜框舞&,表演空间的变化也使得观看和表演的关系偏离了导演的创作初衷,虽然导演加入了打破这场中国表演的“第四堵墙”。、与观众拉近距离的设计:罗巴辛一上来就用中文与观众打招呼;表演期间,管家叶比多霍夫邀请观众一起吟诵表达爱意的歌谣;当疯狂的声音停止时,罗巴辛又跳了出来:“契邈夫本可以在这里停下来,但他写了第四幕。"这些互动吸引了观众不断的笑声。“这些互动吸引了观众的笑声。另外,整部剧的演员很少上下场,整个过程基本没有变化的灯光平等照亮每一个角色,甚至观众台也比普通表演更亮。可见导演为了达到间隔效果付出了很多努力,但由于镜框舞&固有的“神圣感”和观剧礼仪的限制,观众对户外环境失去了自由感,略显僵硬。
现代诠释中 角色之间的关系是无序的
无论是视觉上还是听觉上,这个版本的《樱桃园》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就是“现代”。在19世纪末的俄国庄园里,舞蹈设计没有图解原剧中的物理空间,进而构建了一个源于剧本却极其简单的写意空间。随着表演的不断移动、排列和组合,三个弯曲成树形的华丽灯架,三个笔直的铁轨,以及从整齐到凌乱的椅子。一直在场的摇滚乐队源于剧本中反复提到的“犹太乐队”。叙事节奏在音乐中起伏不定,幕间传来的歌曲也将人物难以形容的内在外化。第一幕开始,柳鲍芙回到庄园后,演员们唱了同样的歌词,但每个人的处理都不一样——罗巴辛停止了说话,柳鲍芙假装开心。非现实的场景让人物从遥远的特定时空中抽离出来,进入特定的矛盾,让观众觉得这样的故事还在重演,他们也在其中。
《樱桃园》可以称之为一部群像剧,似乎与对方无关的事件交织在一起。导演罗德里格斯增强了这种失序感,让他活在当代人的生存中。在他看来,每一个角色都应该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他们的和声形成了这个复调戏。在整部剧中,最明显的改编是杜尼亚莎、雅沙和叶比多霍夫这组经常被忽视的情感关系。起初,杜尼亚莎激动地反复告诉大家,叶比多霍夫向她求婚!可没过多久,跟随主人从巴黎回家的雅沙就用花言巧语俘获了她的心。三个人之间没有狗血的矛盾,联系的暗流都隐藏在语言之下。当比多霍夫起曼陀林向杜尼莎求助时,她和雅沙跳舞,两人越来越近...此时此刻,慵懒奔放的法国感情展现出来。
他的作品中的人物让我们感到亲近,这就是契邈夫之所以让人感到亲近。她们的爱,她们的痛苦,她们的喜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我们是当代人。"(摘自伊利亚·爱伦堡的《重读契邈夫》)纵观整部剧,最现代的角色是夏洛蒂莫。她有一段自我报告的独白:“我没有人可以谈论它。我总是孤单,孤单,没有亲戚朋友。我是谁?为什么我还活着?我甚至不知道……”100多年前,契邈夫利用这位女家庭教师的口中,天才似乎说出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孤独而荒谬地寻找存在的价值,质疑存在的虚荣心。
在这个版本的《樱桃园》中,夏洛蒂穿着鲜艳的红色连衣裙,在昏暗的舞蹈&基调上极其显眼,但她总是一个人在事件之外,似乎被刻意削弱了,但导演给她增加了一部原剧本中没有的剧——她向老管家费尔斯坦白。新与旧,年轻与衰老,荒谬或独特...导演给观众留下了解读的空间。
正如罗德里格斯在导演的解释中所说:“樱桃园是关于一个尚未完全理解的新世界的痛苦和希望。”通过这部剧,契邈夫告诉大家,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沉沦悲观,而是要大声喊“你好,新生活!”(朱彦凝)
拍摄/Christophe Raynaud de Lage Festival d’Avignon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