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人开始独自旅行时,出走的决心
【编者按】
电影《离开的决心》正在上映。咏梅饰演的主角李红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女性,在大银幕上很少见。她日复一日地被困在家务中,丈夫的压制和对孩子的期待几乎是她生活的所有背景墙。在抑郁症中,她暗暗计划离开,但她仍然因为家人而无法旅行。最后,她决定不再等待,独自上路。
这个故事是根据苏敏的亲身经历改编的。苏敏住在郑州。57岁时,她离开了丈夫、女儿和外孙,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旅行。旅行一年后,她参加了《涟漪效应》播客的录制。她在对话中说,通过旅行,她摆脱了“今天可以看到最后一天”的生活,成长为一个新的自己。本文摘录了一些播客内容,讨论当一个女人独自旅行时,这对她意味着什么。
对谈人:
“57岁阿姨自驾游全国”主角苏敏,2020年,她独自从河南出发,自驾数万公里到达海南。
多年记者陈竹沁(竹子),Belonginging线下互动平台 Space创始人之一,长期关注性别和精神健康的话题。
出版女性真实故事集《木兰完婚》的胡卉,非虚构作家。
"一个人的旅行,可以与世界直接相关"
葛书润:有没有一次竹子老师去旅游的经历,去了哪里?
陈竹沁:由于我以前也是一名调查记者,在工作中有很多独自出差的经历,所以如果真的打算出去旅游,还是会和朋友一起旅行。唯一一次一个人旅行太神奇了。我被我最好的朋友放了鸽子。当时我本来要去日本玩的。然后,海啸和核泄漏刚刚发生在日本。我最好朋友的丈夫担心不安全。她已经和我一起买了机票,但最后还是退了,于是我变成了一个人,去东京玩了一个星期。
我认为这可能与东京的城市文化有关。一方面,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活特别丰富,整个城市的设施对独自外出的人特别友好,你不会感到任何不便。但与此同时,当你独自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旅行时,你可以感到寒冷和孤独,我非常喜欢。
葛书润:胡卉老师有独自旅行的经历吗?
胡卉:有一年,我自己去了新疆。当时刚硕士毕业,二十五六岁。我刚参加工作。我必须挥霍我的工资。我自己去了北京,一路去了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布尔津和富蕴县。我在那里呆了十几天。
我跑出去的时候,好像运气一般都不错。南迦巴瓦峰积雪了很长时间,一直雾蒙蒙的,不容易看出来。那天早上,我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看到了南迦巴瓦峰三次。有一次,临近中午,太阳是金色的,很美。
我一个人去新疆的时候,坐了很久的公交车去克拉玛依的魔鬼城看日落。那时候天已经太晚了,夕阳几分钟就会落下,所以下车后一路跑来跑去。魔鬼城是风蚀地貌。那些山被风吹得很奇怪。你越往里跑,就越可怕。当时我身边好像没人,就自己跑到了最高的山上。

克拉玛依胡卉看到的日落。受访者提供图片
奇怪的是,当时我在跑步的时候,心里好像一直在想当时在上海遇到的一点挫折。那时候我刚开始工作,还没有完全适应。我的身体在新疆跑步,但我的心似乎还在上海受伤。然而,我记得当我一直在恶魔城跑步时,我的心似乎有一种拒绝的精神,我认为我仍然必须尊重自己,或者在许多选择中坚持自己。
那一刻,似乎很神奇,仿佛自己在大自然之间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当我一个人跑到高山时,夕阳出现在我面前,非常丰满,真的很美。我觉得我好像抓住了上帝的礼物。
一次旅行,能与世界有非常直接的联系,就像一次对话。反而感知能力会更强,感觉也会很深。
葛书润:感觉这对你的人生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旅行。
胡卉:我不太清楚旅行中发生的深刻感受。后来看了一本瑞士人写的关于旅行的书,叫《世界之道》。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对那种神奇的感觉描述的挺准确的,也很诗意。
他说:“不是家庭,不是职业,也不是别人对你的看法,而是大自然中为数不多的时刻。”那一刻“从时空的浮动中升起,比心中的爱更安静,这一刻如此珍贵。当生活分配给我们时,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只是填满了我们虚弱的心。”当时好像被这段话抓住了,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还是挺喜欢独自旅行的,因为自己的性格很容易照顾到身边的人,当我和别人一起出去的时候,我总是在嘘寒问暖。
葛书润:但是一个人的时候不需要照顾别人,只需要注意自己内心的感受。
李泞伶:苏阿姨,你一个人在路上驰骋时有什么感觉?能不能描述一下?
苏敏:我更喜欢汽车和驾驶。当我在路上开车时,我的身心处于一种非常自由和放松的状态,我感到非常快乐。而且,满眼的树和路两边的风景特别能感染我,让我觉得特别安静,有一种呼吸自由空气的感觉。

苏敏。 被访者供图
李泞伶:这位澎湃人物之前也采访过你。你把这次公路旅行描述为“一次自由透气”。现在回想起来,这次透气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苏敏:它真的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在我的前半生出来之前,我对生活没有任何希望,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可以看到最后一天”的感觉。但是这次出来之后,不但认识了伙伴,也改变了我的许多认知。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不应该被束缚在家里,去过一眼就能看到头的生活。相反,他们应该找到一些他们从未过过的,他们渴望过的生活。
旅行后,我的身体和思想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说我开朗,逻辑清晰。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在家说话做事都是有逻辑的,但是现在大家都这么说我,这其实是我出去旅游的结果,接触的人多了,锻炼出来了。
感觉现在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由自在。如果我想看风景,我会去看风景。如果我不想看风景,我可以缩在一个地方,在那里呆十天半,好好休息,欣赏当地的风土人情。我觉得今天的心情特别适合。我已经爱上了这种生活。

苏敏在路上开车。报纸记者 曾茵子 图
妇女需要家庭以外的社交网络和公共空间。
葛书润:一本名为《木兰完婚》的胡卉老师出版的书,里面包含了15个有关女性的故事,能不能把这本书介绍给观众朋友?
胡卉:《木兰完婚》这本书基本上就是我这几年在澎湃新闻的非虚构栏目《镜相》上发表的故事,也感谢澎湃。
这里共有15个不同年龄的女性故事。他们有的只有两岁,有的已经60多岁了,有的单身,有的正在结婚,有的离婚。有的人面临着一些困难,有的人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困境。我认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时,他们都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挑战,然后他们也能看到一些人性的珍贵和闪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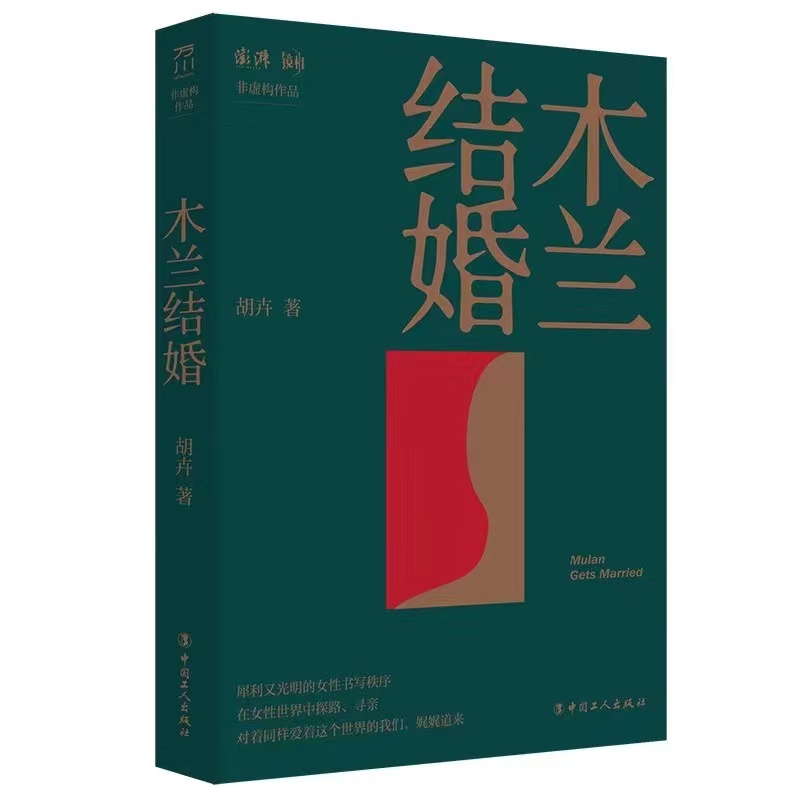
书影《木兰完婚》。 被访者供图
葛书润:这本书的每一个主角都是女性。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意识,专门把女人当成写作目标?有什么启发你的吗?
胡卉:应该是那一年生了孩子,所以发现男女最大的区别就是生孩子。所以我会更有意识地关注性别。
葛书润:你书中的15个故事中有一些是对女性离开的描述吗?就是有这样一个突出的离开女人的形象。这个“离开”不一定是旅行,也不一定是从家里出来,离开以前的生活。你能介绍一两个吗?
胡卉:我写过几个这样的女人,但是她们离开的方式不同。一篇名为《逃离》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子在一线城市安定下来的故事,却发现丈夫有家暴的趋势。她在犹豫要不要带着年幼的孩子离婚。因为这个家庭真的是她设法建立的,她很难这么快做出切割的决定。另外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位单亲妈妈辞去了一位小地方医院护士的工作,要去深圳打拼,工资更高,还带着自己的孩子和母亲。
我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看到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行为自由度更大,但另一方面,她们在移动时携带的物品更重。每次我的写作目标移动,每次我离开,他们实际上都把一些家庭责任带到自己身上。
葛书润:她们并没有把家庭抛在后面,而是会背负着这一责任继续出走。
胡卉:是的,她离开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她没有走出丈夫的家,把孩子和婚姻留在那个家里,而是和孩子一起去了。如今,城市女性有一定的谋生能力,她们习惯于在多年的婚姻生活中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葛书润:这可能已经成为他们的惯性之一。你故事里的这些女人,你观察到她们一般是出于什么样的动力离开的,是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还是想追求个人价值?
胡卉:也许每个人都会想到,对美好生活的希望。但是他们都对自己有信心,才敢于改变,才敢于挑战新事物。
葛书润:你认为当一个女人选择从一种生活跳到另一种生活时,她的负担会比男人更重吗?他们会遇到一些属于这个性别的障碍吗?
胡卉:我似乎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男人也很难。我认为个人和个人的社会似乎很难分类。我们只能看着和分析那个人,她/他是什么样的,他是怎么想的。
葛书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不同的想法。我觉得你刚才的话其实给了我一些启发,就是不要用真实的经验去套一些死板的概念,或者诚实地走向这些真实的人。这可能是阅读文学作品的更好方法。
李泞伶:竹是以前的记者,现在正在做一个线下的公益组织。Belonging space"。在女性权益和身心健康方面,你的偏见与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吗?
陈竹沁:我们的空间是由两位女性共同创造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个人经历慢慢专注于性别问题。我的合作伙伴曾经是一个与身心健康艺术展览相关的公益组织,所以我们想尝试在两个问题之间找到一个交集。
无论从身边的经验还是统计数据来看,女性抑郁症的发生率都比较高,社会结构因素很多,而不仅仅是个人精神的原因。所以我们在做这样的线下空间的时候,一方面想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大家讨论这些话题,通过丰富的文学活动,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归属感,就像它的名字所体现的那样。

Belonging space原来进门的展厅,放了一些公益宣传册。受访者提供图片供图片。
李泞伶:你们在探索自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的方式?
陈竹沁:对于女性旅游这个话题,我确实会从性别的角度来看一些问题,自古以来,女人和男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公共空间往往不对女人敞开,或者自己对女人不够安全。
此外,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中产阶级文化,旅游的自主权往往体现在对财富的控制上。当女性想出去旅游,感受各种文化,认识不同的人,在没有家庭资产实权的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控制家庭财产时打破确定性,这种可能性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出门,比如旅游,是打破常规的概率。旅行可能只是一扇窗户。在这个时空里,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你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和自己交谈,整理很多关系了。
李泞伶:如果说旅行只能是一种短期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你认为处于现实困境中的女性还能做些什么来让这种改善持续更久?
陈竹沁:我想也许更多的是重建自己身边的社交网络。一位美国女性心理学家(珍·贝克·密勒)在20世纪70年代写了一本名为《走向新的女性心理学》的书。她提出了关系文化理论。她说女性的特点是在与他人建立情感和归属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可能不同于以个人发展和竞争为核心的男性。而且女人会反过来被指责“依赖性强”,或者被指责把这种归属关系作为生活的中心。许多妇女患抑郁症也与这种归属关系的丧失有关。
密勒认为,女性在社会上唯一能得到的归属方式就是一种屈服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多的是寻找另一半的肯定。但是,他们不应该谴责自己内心对这种归属感的渴望,更重要的是重构这种归属感的本质。首先要决定和谁联系,问问自己,我是谁,我需要什么,我真正想决定什么,从而重建新的社会规范。这样一种新的归属关系和行动力可以相互融合,促进女性携手合作,集体行动,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力量。
把旅行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旅行,或者我和一些陌生人和新朋友一起旅行,也可能是重建网络社交的一种方式。
旅游业不必昂贵,每天“出走”也是治愈的。
李泞伶:竹对心理健康领域比较了解,旅游能不能成为一种治愈的方法?
陈竹沁:目前,英国的一些精神健康机构会给出一些所谓的“社会处方”,这与直接服用的身心健康药物不同。它把人们放回一个人际交往的环境,与自然相处。例如,花一些时间在图书馆看书,或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或在大自然中徒步旅行。这本身就有一种治愈作用,能营造出一种与你日常生活中那些烦恼的东西相阻隔的氛围,找到一种内心的宁静。即使有时候只是出去,也就是去身边的公园,或者在院子里散步,把它当成一种新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一种特殊的行为,你也会更有效地治愈自己。
葛书润:我想问苏阿姨,就是听说你在这次公路旅行之前,其实已经开始录制直播视频了,然后你觉得录制视频本身对你出门的这样决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吗?
苏敏:旅行之前没有开始直播,只是开始创作一些短视频,其实是为了这次旅行。刚才竹子老师也说过,这次旅行是中产阶级的事,其实是花钱的事。对于我这个只有2000元养老金的老人来说,支付我的旅行费用有点紧张,所以我想自己做点什么,这样我就可以节省一些旅行费用。
老实说,刚开始做了四五个月,没有任何收入,最多只有几毛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制作这个视频并不一定是为了盈利,它也能记录你的生活。我们老年人有时记忆力差,今年可以忘记去年发生了什么。但是因为短视频的记录,我可以随时翻出来看看去年今天在哪里,做了什么。事实上,短片对我的生活也是一个很好的记录。
今年(短视频和直播)确实对我的旅行有帮助。随着粉丝数量的增加,我的窗户里放了一些商品,有些人买了。这个收入也是对我旅行的一点支持。
但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居然学会了用手机记录下来,用相机拍下我眼中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苏敏边做饭边直播,吸引了不少骑手观看。
葛书润:一方面我觉得你很接地气,另一方面我觉得你一路上的经历也很浪漫,就像一部公路电影,听到我就很感动。
苏敏:我真的像一部充满快乐、新奇、曲折、一些困难和烦恼的高速公路电影。总之,它是成千上万个世界的写照,是现实生活的记录。我觉得拍电影可能很精彩。
苏敏:我想问两位老师(竹子和胡子),你觉得我现在在路上公路旅行怎么样?很多人会说,作为一个女人,她应该在家照顾宝宝,照顾丈夫和孩子,不能有自己的生活。我的直播间里有人问我:“你这样抛弃家庭和女儿舒服吗?”
陈竹沁:尤其希望妈妈能看到苏阿姨的视频,然后希望她也能为自己而活。我觉得这应该是我身边很多女生的共同感受。因为有时候,很多母女之间的分歧都存在于母亲太在乎孩子了,你怎么还没结婚,为什么不让我抱孙子之类的事情上。在我看来,我们上一代的母亲,就是包括苏阿姨也说,即使想出去自由地生活,其实心中的羁绊依然存在。但是我会对她说:“没什么事,我自己也能搞定,你出去玩吧。”
葛书润:也就是反而希望妈妈把这个目光分散一点,不要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
陈竹沁:是的,反而压力很大。我们都希望妈妈能出去走走,但同时也希望社会文化能给她们精神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出走”的配套设施可以更好,比如城市的公共空间可以更安全,对女性更友好。在push中,我们不应该把“出去走走”这件事变成另一种新的社会规范。现在我也觉得应该多陪陪妈妈,带她出去玩,或者在家帮她做一些家务,从身边做起,从了解妈妈或者女长辈开始。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