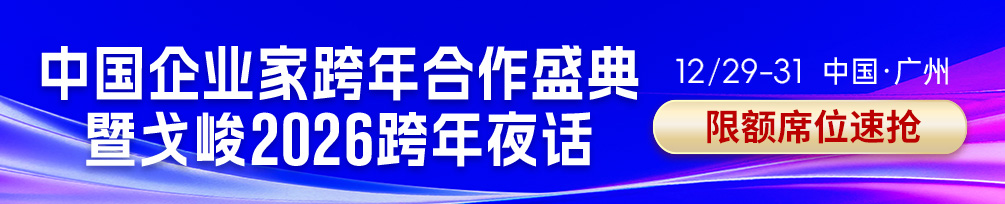牵牛花染姜梅的尝试与感悟
魏芳芳
六月,梅子黄熟,挑选红晕浓重的,摘除短梗,洗净后用干棉布擦干,放入陶瓷瓮。按照鲜梅和盐六比一的比例拌匀。几天后,梅汁渗出,用原木小棒轻轻翻搅,再团一抔红泥封缸半月。梅雨结束,选个大晴天,在风口支起竹筛,捞出梅子晾晒两天。发酵过的黄梅酸中带甜,装进瓶子,随吃随取。坛子里的梅卤,则化作了让人口齿生津的梅醋,等待着另外两样东西入瓮。

七月,牵牛花开。趁有露水时采摘,剪下绯红花瓣撒进瓮中,不久,梅卤就变成了酽酽的红甘露。把新鲜嫩姜去皮洗净擦干,它通身金亮,扔进坛中,让梅卤水没过姜头顶。腌到透心红,用干净筷子夹出,就像一枝枝红珊瑚。再经过蜜渍,便是可口的蜜饯。红花瓣捞出捣碎,还能做点心。
我在翻读牵牛花古诗文时意外发现,牵牛花有一个极美的实用之处——染织物、染蜜饯,尤其是染嫩姜。

杨万里说“浪言偷得星桥巧,只解冰盘染茈姜” ,梅尧臣也写过“持置梅卤间,染姜奉盘羞,烂如珊瑚枝……” 。清末归隐长沙的大学者王闿运专门写了《牵牛花赋》:“采花浸泉,为染姜梅……点姜梅而相莹,又芳蕰而盈盂。”据说他没钱买花,到处搜罗野花来种,牵牛花就是其中之一。女眷们还会摘来戴,“花时侵晨,对妇晓妆,乘露簪鬓,明丽清艳”。
既然前人都说牵牛花染姜梅色美味佳,我禁不住“红鲜可爱”的诱惑,四处寻找做法,终于在《永乐大典》卷 2811 “梅”目录下找到具体做法,可当时是隆冬,既无梅也无花。

中秋时,我与家人聚在寿春兰草农庄。清晨漫步,露水微凉,稻穗扬花,田里稗草结了紫穗,高过稻层,远远看去像流淌着绛紫的雾。往东走,晨曦中一团团紫烟,竟是怒放的牵牛花。成千上万朵牵牛花让我想起梦寐之中的姜梅古法,我赶忙返回,找来竹篮,邀姐姐们去采花。田边沟壑肥水足,牵牛花大如小碗,攀在野草灌木上,像紫霞仙子般盈盈可爱。但采花并不容易,沟深,里面有很多辣蓼,人只能往前探;藤韧,牵一发动全株,久未下雨,一抖泥灰纷纷。毛虫、洋辣子还会冷不丁掉胳膊上,辣得我们一惊一乍,跑去附近农家找牙膏涂抹,痒痛仍不能止。
花是要戴的,姐姐们的辫子上插一朵,我的帽沿上缠一串,有只绿色小蚱蜢,四脚扎进花瓣里,见人也不逃跑,花儿走它也走。忙了半天,日上三竿,竹篮里只有浅浅一层花,我们四张脸早已红透,一身汗和浮灰。
趁花瓣还鲜,回去赶紧用清水淘洗沥干,用小石臼捣烂成泥,攥出汁水装入瓶中,得到半瓶色泽红紫的原浆。
下午去霍山,在诸佛庵深山里的原三线兵工厂旧址,如今这里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家村。我们住的民宿是村民老许改造的原办公楼,对面墙上长了绿苔的大礼堂展览着驻村画家的作品。南瓜随处爬藤,硕大的黄花开在路边,摇曳在百年枫树干上。老许家半山有小菜园,山根处有几畦姜,长得像小竹林一样茂盛。我心跳加速,感觉它们等我很久了。老许的母亲正在菜园摘红辣椒,她穿着酒红色格子衬衣,霜白的短发向后梳得一丝不乱,看见我满脸笑容,问我要不要辣椒。我谢了她,问能不能要几颗姜,她笑眯眯地让我自己拔。山地的姜贴地紧,拔起来很费气力。

黑土里的新姜鲜白,有粉红的笋芽,斜阳一照,能透见饱满的汁水。洗净后连皮切薄片,用白醋和盐腌制半个小时,再倒进牵牛花汁浸泡,姜色变成殷红,如葡萄酒。厨房里老许夫妻俩和大儿媳妇正忙着做晚餐,民宿还有不少客人。老母亲坐在厨房门口不慌不忙地剥大蒜瓣,还照应着摇窠里六七个月大的小重孙女。她疑惑地看着我把姜装在小白瓷盘中。

大姐记录了我“土法炼钢”的全过程。
捞出的嫩姜呈银红色,放在摆满浓油赤酱的徽菜桌上很养眼。但众人浅尝辄止,知道是牵牛花染色后,只夸好看,不肯多吃。大家的兴致都在老许做的板栗烧鸡、红烧土猪肉、小溪鱼和清炒南瓜花上。说实话,捣碎的牵牛花气味陌生,掩盖了姜香,盐和醋还浮在表面,寡淡得很。古法漫长,从制梅卤到姜出坛至少要三个月,而我断章取义,以醋代梅卤,“姜梅”实为“姜醋”,只花了半日,就像给仔姜泡个红花澡,能好吃才怪!
剩下大半盏碟花染嫩姜无人问津,嫂子舍不得浪费,把汁水滗掉,重新放酱、冰糖、香醋,浸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捡出来,淋上麻油,配绿豆稀饭,众人三两下就光盘了,给附庸风雅的我上了一课。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