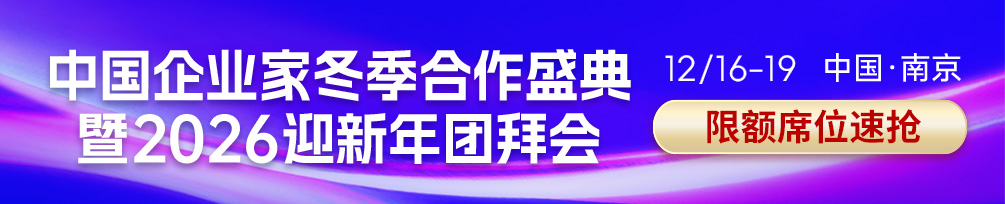张飞彬|北石窟的佛

北石窟的佛

看看你的表情,从百年积累的斑驳中感受到参禅的智慧,我佛慈悲。
听听你的梵音,从四季轮回的节奏中领悟生命的丰富多彩,宇宙的和谐。
触摸你的墙壁,一沙一砾地诉说着建筑的过去,记录着教徒的虔诚。
崇拜你的信仰,一言一语地祈祷众生的苦难,容纳世间的无常。
1
初秋,晨雾萦绕在山腰,覆钟山下飞驰的车流碾碎了秋日的晨光,却很少有人停留。时代就这样把人拉到了忙碌的下一站。只有当孩子晕车时,他才和朋友阿邈停下来,站在蒲河与茹河相遇的堤岸上,欣赏着微风中峡谷流岚飘落的变化,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之间浏览着季节变化的色彩。
不经意间,我抬头看着山顶,阳光透过云层轻轻地洒在地上。突然,我觉得这座覆钟山像镀金的佛龛一样闪闪发光。看到身边的北石窟寺,觉得这一幕应该重复了1000多年,但发现的时机可能转瞬即逝。突然觉得奚康生派出佛寺的那群人应该是那么幸运。
公元509年,陇原大地在北魏历史上经历了一场风云变幻的暴动,让世界更加动荡。奚康生带着朝廷的意志,斩草除根只是英雄的一种冷酷的杀戮方式,无处不在只是皇朝残酷统治的注脚。
叛变很快平静下来,但只留下无尽的死亡和毁灭。他可能再次被噩梦惊醒。那些无辜的死者和血腥的战场困扰着这位王国干部的睡眠。安置灾民可能需要时间。只有安定不安的心,向朝廷表明信念,他们才能不停地往前走。
不难想象,在1500多年前的一个安静的早晨,一个德高望重的和尚毅然接下了奚康生的使命,把建造石窟佛寺作为继承佛教、保护全民生命的选择,于是在统治的边界上找到了一个风水之地。一群人来到覆钟山下,初升的太阳透过薄薄的云朵照耀着大地。他们抬头看着五颜六色的日出,从山顶射下。他们应该看到佛光万丈,僧人觉得“山是佛,佛是山”。大家在这里徘徊一天,下午夕阳余晖,覆钟山沐浴在夕阳中,仰望这座山,更觉得这座山是佛。所以坐东朝西的方向和裸露的悬崖敲定了这个位置。
时至今日,在朝阳中,在微风中,初升的太阳从山顶照射下,五颜六色的晨光从覆钟山的山顶倾泻而下。我们应该能够理解,在成千上万的金光中,他们似乎真的看到了佛光的照耀,理解了佛祖的若隐若现,理解了“山是佛,佛是山,佛是相互交流的。“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我们可以欣赏西边石窟的佛影建筑,东边的道路像银蛇一样蜿蜒。1500多年来,晨昏在砂岩洞穴中运转。工匠的汗水、和尚的冥想和游客的惊叹在光影中重叠。山风掠过佛的耳垂,带着北魏的祈祷掠过我的眉睫,理解信徒前所未有的虔诚,感受这种跨越千年的神圣与壮丽。
2
踩着印满千百年香客虔诚的青台阶,越过石窟寺的山门,从一边的台阶来到七佛石窟(165窟),燃烧了几千年的香烛已经消退,留下了无尽的宁静和佛陀的沉默。一个巨星矗立在洞外两侧。岁月的侵蚀不再清晰,眉宇间怒目而视。凝聚了几千年的庄严,至今依然如火如荼。敬畏是游客的唯一选择。
洞穴中的七佛是视角和信仰的核心。它们按照“3-2-2”的分布放置在东南北三面墙上,仿佛在默默地讲述佛的前世。阿邈能准确地告诉其他佛像代表谁,那些是威胁菩萨,那些是弥勒菩萨,那些是普贤菩萨,那些举着日月的是阿修罗。他们站在这个黑暗的石窟里,仿佛在等待命中注定的人的到来,为他们点亮理解的灯光,引导世界摆脱出生的困境。仰望洞穴的顶端,在色彩斑驳中领悟佛祖的故事,阿邈说:“洞穴里的壁画大概就是舍身养虎,割肉贸鸽,降服火龙的故事。”大概是通过图片来传达佛法的本质,最容易到达人们的内心。
不难想象,几年前,不同朝代的人在这里挖掘悬崖,描绘追求中的理想世界,吸引着修行者沉思和绕佛星期。北石窟寺是宗教活动千年的绝响,聚集了多少知名和尚,在这里修行了多少道德高尚的人。它甚至可以将佛陀的语言刻入砂岩的质感,成为时代跪拜的具体形象。对于在这里生活了几代人的人来说,他们不知道七佛的故事和佛教的故事,但他们深信菩萨能理解陇东方言中的祈祷和内心的虔诚,就像供奉的莲花灯一样,总能照亮无数虔诚的眉毛。至少长期安慰这一方民众的信念,是这一方民众无穷无尽的文化根系。如今,那些迷失在经典中的和尚和美德,最终变成了人们口中的“唐代佛爷”和“西夏罗汉”的乡村传说,甚至没有院子里永恒的古松。琥珀色的松脂从树皮下涌出,仿佛古往今来的祈祷在这里凝结成了晶莹剔透的舍利。
经过长时间的拖延,石窟的佛像大多是斑驳的,看不清楚的佛的尊容似乎在说“佛可以是模糊的,信仰也可以是模糊的”,仿佛在告诉世人,真正的信仰从来不在于形式的清晰,而在于灵魂的感知。我们只是走在这个世界上的小众生,更多的时间可能只需要一个想象,然后那些陆地的神龛、雕像、绘画有一种神秘的美感动了我们的心,我们想象原来丰富多彩的色彩,光滑的线条,庄严的态度,虔诚的信仰,未知的期望。所以在这个峡谷里,在这条河边,信仰和期望一起咆哮。
3
与阿邈交流半天,我大概能够理解历史文化遗迹背后的逻辑。学术界提出了中国石窟带的概念。我把石窟带放在地理和历史的地图上。这个地区也和降雨量的分布有着微妙的联系,正好在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交汇处,恰好在农牧交汇处,与丝绸之路完美重叠。更令人惊叹的是,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下,汉族的精致和包容,少数民族的豪爽和敏捷,在石窟的雕刻和壁画中交织成生动的历史记忆。农业文明的沉稳与秩序,游牧文明的自由与奔放,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共同的表达方式,凝聚成一种独特的艺术瑰宝。
少数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刚刚从奴隶社会迅速进入更先进的封建统治王朝,也带着少数民族以前奴隶主的思维。有一段时间,“把汉族当成胡族耕种的奴隶”的固执思维挥之不去,只能找到新的或更简单的思想来丰富社会意识。佛教已经成为这群执政者的首选。这种对佛教的青睐,表现出与前朝的分离,创造了与当地宗教文化的差距,证明了他们在这个时代创造了所谓的先进与合理。
北魏还没有结束,太武帝阶段的“太武灭佛”应该是历史趋势的调整。唐朝之后,当佛教力量过度膨胀,影响王朝经济社会秩序,威胁王权统治时,宗教可能不得不为王权让路。唐朝以后,佛教只是王国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信仰元素,融入了普通人的万能祈祷。因此,北石窟唐宋等朝代的石雕拓展更多地被称为神龛,中国神话故事被添加到壁画中。
这类佛像不只是石壁上的艺术造型,更多的时间可能是一个王朝的精神图腾。宏伟的建筑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占领,也是文化和精神的统治。它向公众宣示了执政者的伟大和神圣。直到今天,它仍然诉说着执政者对不朽的渴望,对秩序的追求,对永恒的憧憬。然而,在时代测试的浪潮中,皇朝的统治只是过去的云烟被史书轻轻翻过,留下的统治印记也变成了今天的精神内核,成为文化中神秘而温柔的“东方微笑”。
4
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北魏所处的南北朝应该是一个绝望的时代。而且,从东汉末年到隋朝,这种战争纷争和朝不保夕的动荡从头到尾已经持续了近400年。近四个世纪的灾难可以让一个民族对出生失去期望,改变文化信仰。在这样的绝望中,把目光投向来生和永恒是唯一的安慰。
佛说众生皆苦。这种痛苦来自于人本身的“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恨会、爱与离别、五阴火”。然而,佛陀忘记了世界的痛苦,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了一个人的头上,这是一座一个人一生都无法翻越的山。在时代的洪流中,每个人都像被驱使的尘埃一样无法战斗,随波逐流。
在分裂的王国中,上层贵族和社会精英仍然可以谈论和隐逸,创造所谓优雅飞舞和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留下无数浪漫的故事。那么,面对时代的压力,世界上挣扎着生死边缘的人能退到哪里呢?背后只有无尽的艰辛和苦难,就像无尽的荒野和不可预测的深渊。
几千年后,我们再次翻看历史。“尸骨掩野,百无一存”是阶级、民族、皇室宗族之间不断上演的杀戮,只留下“路断了,千里无烟”的建筑。我们也可以理解,面对恐怖绝望的时代,面对佛像和宗教故事,渺小的众生应该有多复杂。似乎只有狂热的信念和温柔的梦想才能掩盖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
5
石窟旁的崖柏年年枯荣,山门飞檐铜铃代代相传。与南石窟寺相比,北石窟是幸运的。100年前,美国华尔纳一行在平凉南石窟砍伐破坏了20多尊造物,小偷团伙在敦煌留下了满地的泥塑碎渣和破碎的佛像。也许是时间的原因。当时他们的观点是南石窟一定有北石窟,所以北石窟在清末的动荡中继续荒芜,在世界的苦难中沉默。北石窟佛像完整,这是命运的垂怜,还是地理上的意外?我们不知道。如今,在敦煌研究院的管理下,文物保护工作者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材料,一点一点地填补壁画上的裂缝,一个接一个地修复佛像。一群人用双手编织一张温柔的网,轻轻地支撑着历史的碎片,让文明能够延续它的诉说,让文物讲述他们的旧事。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祖先们一斧一锤地凿出了佛的故事和信仰,历史的信仰仍然警告着今天的世界。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持续文明的故事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和创造。看看今天的文化载体,工业产品只是消费浪潮中的一个瞬间,建筑只是使用寿命中的一个奇迹。所以,在文明的过程中,今天我们留给百年后的人类是什么?文明之旅中永远存在的风格是什么?供百年后人们欣赏、猜测、思考、憧憬。
原题:《张飞彬|北石窟的佛》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