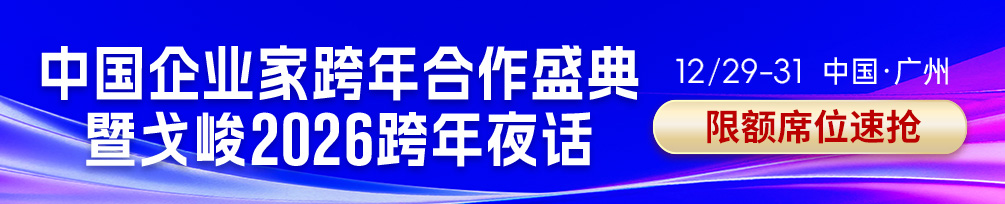运河边,在花巷(杜怀超)

多年后,我到达了花巷。准确地说,我到达了姐姐家,她住在河下镇的花巷里,河下古镇紧挨着运河。如果运河是一条古老的藤条,那么河下就是她藤条上的一个水果。
以前我和爸爸一直住在洪泽湖西岸,说起来也算是在运河旁边。里运河水,无非就是黄河、淮河之水,而洪泽湖则是它们的储水湖。当里运河水位较低时,必须依靠洪泽湖进行补水,当水位较高时,多余的水流入洪泽湖。从某种意义上说,靠近洪泽湖,就是靠近运河、洪泽湖水,也就是运河水,我们已经接触到了运河的边缘。因此,运河的水声、光影和远方的帆船在汹涌的水波中倒影。只要我和父亲靠近洪泽湖,俯下身子,就能看到运河帆船众多,南船北马的兴奋与繁华。虽然我们不能走进历史上九省通衢的清江浦,但我们身边的运河桨声和人语从未停止过。
爸爸是个丈夫,少年时独当一面,摆渡,钓鱼。大江大河自然不能去,小河小溪必然会有父亲的身影。那时我们的身份,应该定位为渔夫,以湖为生。因为曾经湖里的鱼比地里的庄稼多,只要人们站在洪泽湖的大堤上,等一会儿,就会有鱼从水面上甩尾巴,跳到河堤上,吓了人一跳,然后就开心了。爸爸一大早起床,首先要做的就是背着鱼篮,提着撒网朝洪泽湖大堤走去。我和姐姐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爸爸早就把装满鲫鱼、昂刺、鲶鱼等鱼的篮子带回家了。妈妈坐在屋檐下,抬头望着父亲在晨光中晾干渔网,手也不闲着,案板上早就杀了一堆鱼。妈妈举着一条大大小小的鲫鱼,对爸爸大喊大叫,你看把鱼子和鱼孙都抓回来了。爸爸有点脸红,说话,渔网洞眼我已经织得很大了,也不知道这些小鱼小虾怎么还会钻进来。捕捉小鱼小虾作为渔夫,是一种行业禁忌和屈辱,这也是所有渔夫都遵守的约定。身为渔夫的妻子,自然知道鱼儿放生的道理。
这是运河通过洪泽湖展示她温暖的一面。小时候,我见证了水灾的疯狂。当时我们住在湖边,房子叫茅草房,也叫庵棚。它是由泥土胚胎、湖中芦苇和岸边的树木混合而成的。这种房子不坚固,风雨交加,到处漏风漏水。它支撑着房子,这样它就不会崩溃。它是站在地上的四根柱子和爸爸宁愿弯曲的脊梁。
我在花巷荒地度过了一段时间。那时候花巷 58 号码已空了。最后一批房客才走不久,下一批房客还没到。碰巧在这段时间里,姐姐把房子留给我暂住。那是原来姐姐的新房子,那时姐姐一家早就搬到了别处。房屋简陋,接地气很好。墙壁四周是石头堆砌的,厚而粗糙,从外面看,大大小小的石头,就像大大小小的补丁。屋顶不高,灰瓦铺在上面,仿佛与地面上的一块石头连成一片,给人一种矮小塌陷的感觉。院门不远处还有一口四季不干的井。早上或晚上,井的边缘总是挤满了人。淘米、洗衣、打水、杀鱼,还有人除了从家里抓一把花生,边吃边和别人聊天什么都没发生。井是古井,水是活水,因为这口井沿着石板路下来,在几块石头的尽头,就是浩浩荡荡的运河。穿过整个城镇烟火的河流,就像有人把一块丝绸披在它的肩膀上,妖娆而多情。
我喜欢这条花巷,包括门匾上的铭牌:花巷 58 号。那时姐姐出嫁,从洪泽湖大堤搬到这儿,一定也被这座诗意斑驳的房子所吸引。石头堆砌的房子,稳重,再大的风雨也不能动摇它,就像憨厚的姐夫一样,姐姐找到了属于她的港湾。房子唯一引人注目的是木格窗,雕刻的立体木制窗花,两只喜鹊。在三几个暗红色和墨水的影响下,房子简单而深邃,仿佛古装剧的场景瞬间出现,心中的美好和诗意一下子打动了姐姐内心的柔软。嗯,就是这样。姐姐指的是她的新房子。更为重要的是,姐姐在转身的那一刻,和我一样,站在院门口,一眼望去了那条玉带般的运河,温顺而迷人的河流。
大家都是在湖边长大的,也可以说都是在运河边长大的。事实上,洪泽湖或河下,都只是运河在漫长的旅途中留下的一个光点,我们都生活在那个明亮的地方。不只是我和姐姐,还有爸爸,妈妈和岸上所有的人。院门开着,就是运河。即便我们并非诗人海子所说的“面向大海”,也同样“春暖花开”。院子里是炊烟,生活,院子外面是运河,远处和无穷无尽的大家。
姐姐把自己的一生都放在这个院子里,自然有她的道理。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从漂泊到落地。即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恐慌和焦虑中度过,我们也从未失去信心和生存的力量。我相信全身晒黑的爸爸,紧握船桨磨出厚厚老茧的大手,在风浪中摇晃时总能安全归来的渔船。这些促使我和姐姐在未来面对生活的大风大浪时,总能从容面对,充满憧憬。另外,在她身边,还有一条熟悉而又陌生的运河,这也是姐姐对自己的新房——三间石屋留下的肯定答案。
生活在河下的姐姐,和镇上的人一样,踩着琵琶般的石头,沿着河流般的街道,一脚一脚地把日子交出去。
之后,我在花巷住了半年。这个原因是姐姐一家搬到了另一个地方,从石屋到宽敞明亮的独栋建筑,留下了空荡荡的房子和寂静的运河。自然,这也和姐姐、姐夫的能力有关。那时候姐夫已经从运河边的一家水泥制品厂买断出来,把水凝固成水泥的日子,还不如跟着河流一起去远方。我想我姐夫也从运河的光影中看透了这个秘密,一个美丽的蜕变,就像一朵自由的浪花融入了滚滚的海浪。当他再次上岸时,他已经有了三两栋两层的小楼和一栋商品房。
那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从院子里出来,走过古井,穿过巷子里森林般的眼睛和身后的窃窃私语,就像一条隐秘的河流,伴随着我。我顾不上理睬,直奔院门口的运河。我喜欢河流的包容、接受和沉默,仿佛它理解我的想法。它把我的倒影投入到波澜中,不出声,不打断,不干涉我的散漫。它只是自顾自地,沿着河流向远方走去。那时候我正处在人生的艰难选择时刻,北进还是南进?或者原地不动。原地不动,虽能生活,抱着小日子万般聊天,却不甘心;而且北进或南进,就得丢掉来之不易的金饭碗。前后空无一人,这是多么令人忧郁的时刻。久居樊笼,难免会失去打破护栏的气魄,从而产生依赖。每日早晨,我斜背背着包,双手插在裤兜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在大家陌生的眼神中逃离。独自坐在河边,望着远近的拖船发愣。下午,一个人悄悄回来,关上门窗,在床上对着屋顶睁开眼睛。黑暗中的屋顶就像一条黑暗的河流,神秘而浩瀚,同样深不可测。
严格来说,花巷的生活始于下午。在我孤独、烦闷、无人能及的时候,陪伴我的只有花巷,还有古井、运河、花巷里的每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石屋里,静静地听着门口传递的一切,比如星光、风声、雨声、三两个梦,还有门边的河声。偶尔水滴会从井壁上滴下来,像一粒重金属,砸向夜晚的宁静,从井底发出一声清脆的琴声。而且我,把这琴声当作一个音符,沿着井底潜行,不出一二里,就到了运河。河水在星光洒满水面的午夜翻滚,载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密语。这条人工河流,我常常把它当作地球上的琴弦。沿途的村庄、城市和人间烟火,只不过是它地面奏鸣曲中的某一章或音符。我忍不住感受到了花巷、河下和所有住在运河边的人。一个庭院和一座古城可以整天面对汹涌、壮丽和广阔的河流,所以它将成为广阔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广阔的进出口,就是那座古井。
是啊,古井的下午,就是花巷的下午,河下的下午。古井一声喧嚣,随着一桶水从井底打上,下午的书页就散开了。三三两两的人打开大门,从院子里走出来,聚集在古井里。小男孩,壮年男人,中年妇女都有。话题也是不合逻辑的。过了一会儿,张家的女儿生了一个孩子。西家的男人找到了一个转弯的妻子。听说是船上的。几个月后,他和拖船队一起离开了。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他们自己的宝宝。他们互相谈论他们的宝宝出去工作、工作和做生意的各种情况。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到河边了。说着说着老人还会情不自禁地偷眼,好像有液体流出。
哭泣?有些人会戳破真相。
没有呢?老头子说,刚才的河水溅到眼睛里。
有意思的是,这种龙门阵,总是让人不那么怀旧。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周围的小商贩。隔壁不远处卖茶叶的老板,在食客来之前,丢下擀面棒,走过来加入胡侃神吹的大部队。他坐在角落里,从怀里拿出一个水烟袋,自己抽了起来。他舒适的外表令人陶醉。而且邻近卖大鼓书的,则踱着官步,大摇大摆地来,嘴里小声哼着拉魂腔,旁若无人。整天坐在门口的纸坊老板,姓李,看起来中年了,忍不住身边热闹起来。他从车间出来,为了不耽误自己的工作,顺势把家伙带到井边,一边戴着红灯笼,一边说着几句话。灯笼,为古井的气场增添了许多喜庆与吉祥。难怪他的灯笼不仅技艺精湛,而且种类繁多,如仙鹤灯、孙猴灯、鲤鱼灯、八仙过海灯、麒麟送子灯、马灯等。如果不是因为地方狭窄,不知道真相的人会认为古井正在这里举办灯会。
我买了两个他家的灯笼,挂在姐姐家的屋檐下。它们是红色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像嵌在石墙里的两个布扣子。我最喜欢的是河灯,赶上节气和新年,或者每天毫无意义地买几个,晚上一个人拿到运河边,点燃河灯,看着它在河里渐渐走开消失。
在花巷短暂居住后,我再也没有回到洪泽湖大堤旁的那个村庄,而是转身北进,从运河石码头一路北上,抵进京城。花巷应该是后来作家徐则臣小说中的花街。他在《花街九故事》中写道:他出生在花街,生长在花街,人在花街,心在花街。这里出走的人和留下的人都是花街的故事。的确,花巷的故事就像运河一样汹涌澎湃,巷口不远处就是吴承恩故居,《西游记》这本神书就是从他的书里出来的。若稍加注意,街头巷尾,你就会看到西游文化已经深深地嵌入其中,石柱、雕塑等建筑,总要包含美猴王。再往前走,还会看到镇淮楼、中国水运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建筑,以及周边梁红玉祠、里运河生态文化走廊;这些运河滋养的风景已经成为历史留下的花束,印记着淮安过去水运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我曾经站在镇淮楼下,凝视着这座昂然的建筑,被它磅礴浑厚的气势所折服。我也深深体会到了这座城市从洪水到淮水安澜的历史。从中国水运博物馆和运河博物馆,我看到各种木船、帆船和远洋船停留在这里。从这里开始,我沿着运河走向四面八方。原本以为,这里留下的不仅仅是故事、历史、文化,还有一种类似血脉的东西,在天下生长。
即使远离运河,远离花巷,花巷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不断地听到家乡、花巷的人和事。当初岸上的小伙伴虎子、宝石、六子、小芳等人也陆续离开了家乡,住在花巷周围。他们有的自己开餐馆当老板,有的在工矿企业工作有稳定的工作,大学毕业后努力学习考上政府部门。当然,越来越多的人从岸边走来。他们围着花巷,围着运河打零工,搬砖,扛沙子,踢三轮,跑外卖,在城市丛林里努力而踏实地生活。
我常常想,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人类的天性,还是运河血液在我们骨子里涌动,注定要漂泊、追逐、远行。每个生活在运河边的人,生命的线条早已烙下了运河滚滚的浪花、帆船和号子。逆流而行或顺河而下。它已成为我或他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四处辗转、漂流、暂坐或停留。尽管当初洪泽湖大堤下的庵棚不在,花巷 58 石屋不在,然后它们被游客织成的古雅迷人的老文化街区所取代。那些留在生活中的浪花,湖边爸爸的桨,远嫁的姐姐,花巷,古井,石头码头,河灯,都是永恒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条滚滚向前的河流,在追逐和奔跑的过程中,走向更广阔的地方,这不正是河流的秘密吗?
(杜怀超,1978 2008年出生,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现在在江苏省徐州市文联工作。有很多作品,比如《苍耳:消失或再现》、《大地书页》、《大地散曲》等。获得紫金山文学奖、三毛散文奖、老舍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孙犁散文奖等。)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