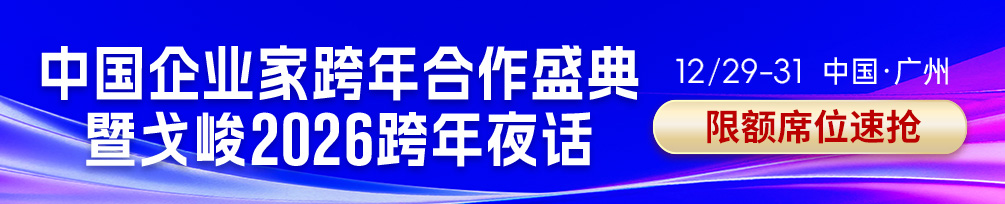世界文化之旅与文化人类学同行。

鲁思 · 1887本尼迪克特(1887 — 1948), 知名人类学家的代表作《菊与刀》长期占据国内社会科学读物的畅销榜。相信在很多读者心目中的“世界文化地图”中,关于日本文化的“拼图”都是本尼迪克特做的。不过,距离《菊与刀》1946 年问世已近 80 2008年,有学者直言不讳地说,它早已“不是一个可靠的导论性作品”(徐英瑾:〈菊与刀〉》)。的确,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双向奔赴在数量和质量上早已不是以前的样子,这自然对我们的文化研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单纯阅读现有的研究成果显然是不够的,更深入地掌握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最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菊与刀》正是作者对自己的看法。 1934 2008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中理论应用的有效性,后者也被认为是从事文化研究的最佳引路书。所以,暂别《菊与刀》,回顾《文化模式》,具有“返本-开新”的意义。
如今,新翻译的文化模式已经到了我们的手中。译者的表达打磨得很好,对原始部落的描述非常生动,值得称赞。总的来说,它履行了一个好的翻译职责:降低读者理解的门槛,提高内容的阅读兴趣。
从理论上讲,作者首先强调,西方文明的全球传播并非一定,而是“历史的巧合”;但是,具有先发优势的民族很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把自己的文化夸大为历史必然和普遍标准。有了中心,自然就有了所谓的边缘。此时,波利尼西亚人从爪哇岛到复活节岛跨越一万公里的文化传媒等其他事实被视为“区域性种族的过度发展”。于是,白人“环游世界,却从未住过国际酒店外的地方”,错过了世界旅行的根本乐趣。至于当今世界,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哲学伦理结论——“因为我们的文明依赖于经济竞争,所以我们说这是人性可以依靠的第一动机”,残留仍然是挥之不去的鬼魂。
实际上,作者指责的不仅仅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文化人类学家眼里,任何自我中心理论都忽略了一点:一种文化是在无数可能的“大弧拱”中被裁定的产物。换句话说,另一套文化选择是完全可能的。意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失去文化想象。在 20 世纪 30 这个时代,本尼迪克特的多元文化观可谓先锋。书中举了两个文化人类学案例:阿帕切人在如何看待性成熟时,将初潮视为神圣,而凯列尔印第安人则避开了他们的年轻女士;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从来没有预防过战争,所以似乎没有任何文化缺乏战争的概念,但加利福尼亚教团印第安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最多只能从街头斗殴的意义上理解当代人所谓的战争。这些案例表明,在类似的生理基础上,世界各地的人选择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但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中同样可以使用,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可塑性。正如作者所说,可塑性是人类“开始并保持进步的土壤”,是人类不同于动物、超越自然限制、实现全球生存的秘诀。与此同时,可塑性需要多元文化观的培养,但后者并非先天给予,而是主要依赖于后天的习得。综合以上两点,可以得出结论:培养多元文化观素养,摆脱自我中心主义不是选择,而是每一个民族的必需品。
所以,如何实际对多元化保持开放?作者给出了一个整体文化观的理论解决方案,即在接触异国文化时,它被视为一个独特而有机的整体,而不是“肢解”它,然后“数”它的特征。从整体上看,它代表着“以制度化的动机、情感和价值为主题观察特定的行为”,考察特定群体在劳动、婚丧、战争等方面的生活实践。在什么样的根本目标的引导下,使其成为一个整合的整体。在这种态度的指导下,作者以古希腊的日神为指导。 / 酒神(控制 / 疯狂)精神是一种视角,比较了三种原始文明,它们所呈现的差异和多样性令人一饱眼福。但是,我想提出一种阅读这本书的方法,帮助读者更好地深入到这本《文化模式》中,而不是剧透书中有趣的民族志细节。
对我来说,“文化模式”至少值得阅读两次。第一次阅读时,我们可以带入作者的角度——一个受德国观念论传统影响的美国学术精英——学习如何像文化人类学家一样观察异国文化,也就是带着质疑文化模式的态度阅读。在熟悉了作者和整部作品之后,我们可以尝试在重读的时候把它从作者的角度抽离出来,从第三者的角度来推敲作者看到的场景和得到的其他含义——“螳螂捕蝉,我们之后”。第二次出发更有趣,因为它实际上是围绕相关案例进行的扩展性研究。因为文化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向通常是极其详细和全面的,我们不妨带入个人或特定学科的问题意识,让这些材料承载更多的探索兴趣。
例如,对于信仰“和为贵”的中华文化来说,推崇嫉妒和仇恨的多布文化恐怕是无法理解的。作者没有深入分析原因,而是在案件的最后总结了多布人:“他们的美德是尽可能地找到受害者,发泄他们对人和自然的恶意。“这种仇恨究竟从何而来?这里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线索。案例一开始,作者介绍了多布人的岛屿“怪石嶙峋,土少鱼稀”,他们与自己的族人保持着“永久的区际敌对关系”。;但是周围那些自然禀赋极佳的岛屿却是一幅政通人和的景象,大家都注重和平与互惠。对于后续的材料,我们注意到多布人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确实相当紧凑。想到马克思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精神生活”的洞察,我认为各种因素很可能是“恶意”的物质根源。如果上述论述成立,我们就见证了根植于田野的文化人类学是如何与政治经济学原理相结合的。
综上所述,文化人类学是一门面向概率和多样性的学科,其实际效用并不局限于特定学科、特定读者。人类学者周大鸣曾指出,尽管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实践并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旅游,但在外部形式上,它们是非常相似的。作者想继续补充的是,文化人类学家和普通游客之间的内在区别,是否具备上述多样性和整体文化观,然后是否真正理解其他文化。虽然大多数读者不需要成为专业的文化人类学家,但我们都可以旅行,文化人类学的滋润有助于我们走出停留在多元文化之外的洞察力,赢得更丰富的旅行体验。或者,人生无非就是一次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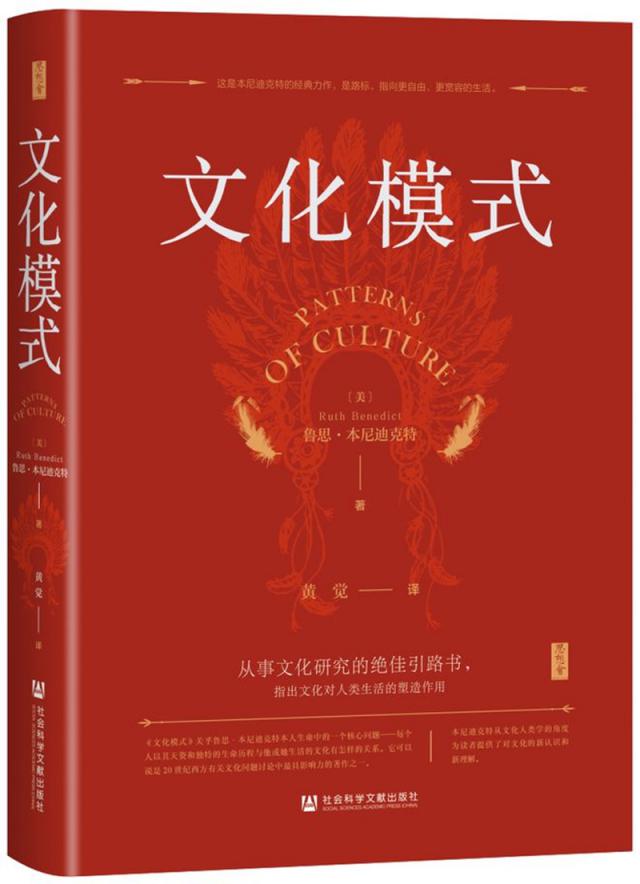
文化模式, [ 美 ] 鲁思 · 本尼迪克特 着,黄 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会科学文献。 2024 年出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