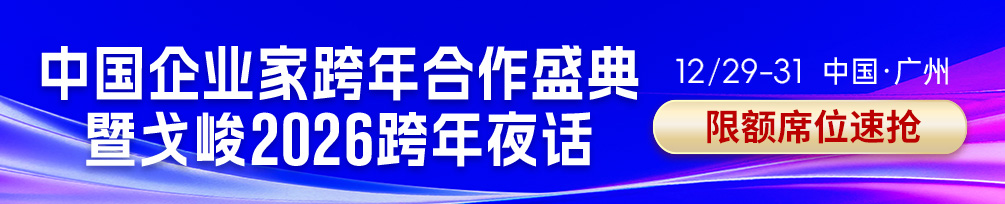这是一部多声部合唱的中国故事。

在简单的民间故事中,上海美影厂的《燃比娃》探索了多样化的动画语言。
今年柏林电影节结束,主竞赛单位中国电影《生活之地》获得银熊奖最佳导演奖。年轻导演景一的《植物学家》在新一代Kplus模块获得评审团奖。同样在新一代Kplus模块中,另一部入围的中国电影《燃比娃》是上海艺术电影制片厂自1982年《三个和尚》和1984年《蛤蜊之争》以来,时隔40年,新作被选入柏林电影节。
从儿童的角度来看,《生息之地》回顾了90年代农村婚礼仪式的习俗,就像一个当代汉文化的民族志向。《植物学家》选择了“植物”的特殊起点,描述了哈萨克文化与风土人情的关系,从孩子的角度想象了游牧民族和汉族相互影响的跨文化童话。《燃比娃》以四川阿坝羌族民间传说为基础,结合艺术史和少数民族艺术史,结合多元化、大胆实验风格的动画技法,重述了跨民族的当代神话。这类作品的共性在于,跳出工业化、类型化的电影模式,关注被商业娱乐所忽视的中国风土人情。关于中国故事的讲述,像“哪一个”一样强大,令人兴奋。但是,“讲故事”不仅仅是一种声音,一种声音,还有很高的主唱,这也需要丰富的和声。这些作品在欧洲电影节的地方被看到和关注,是中国故事的多声合唱。
一个关于“和”的童话: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植物学家》的主角是一个哈萨克男孩。传统哈萨克游牧谋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密切,植物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它不仅用于日常生活,还构成了民间传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植物”也是一个明确的比喻。季节变了,草枯了,就像时间变迁中民族文化的痕迹一样。
导演景一不是哈萨克人,他的父亲从江苏搬到了新疆,他出生在北疆的一个山村里长大。《植物学家》的拍摄地点与景一的出生地相隔一座山。在赛里木湖附近,它靠近中国西北国界线。它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山乡,离哈萨克斯坦很近。起初,他想到的片名是《白屋中的植物学家》,因为传统的哈萨克住宅毡房被称为“白屋”。然而,当他深入牧民社区进行田野调查时,他发现拍摄地附近的哈萨克牧民早已失去了毡房。现代畜牧业将牧民从游牧生活中抽离出来。他们搬到县城,进入城市生活。此外,他们雇佣工人放羊,这已经成为一种工作,而不是一种生活习惯。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和文化的变化不断发生。但在变化中,一定是新的替代旧的,外来替代原生?
因此,《植物学家》想象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代际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相互影响。导演形容这是一个关于“和”的童话故事——哈萨克和汉族、游牧和中原、自然和现代。这两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加法的共生,就像郁郁葱葱的植物。整部电影中都分布着植物的形象。这部电影的小主角,一个生活在山村的男孩,与自然息息相关。他通过植物、河流、土地和动物感知世界。他的哥哥在城里想念这个村庄,但这个村庄只能是他生活中的“暂停”。他想很快回到城市生活。他受到现代的诱惑,怀念传统。小男孩长大后会不会变成另一个“哥哥”?导演认为,弟弟和哥哥,以及在这个家庭中做出不同选择的亲人,就像一株植物,一棵树枝朝着不同的方向生长。村里,男孩的生活和一个汉族女孩有交集。男孩听奶奶唱哈萨克民歌,女孩听茉莉舞。当茉莉和哈萨克民歌相遇时,汉族和哈萨克、汉族文化和游牧文化就像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植物在风中交流。
景一说,他更愿意相信,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有一个时刻,就像电影中青梅竹马的孩子并肩而坐。他把《植物学家》描述为“一个当代童话,也是一种祝福”。
挑战商业电影惯性:在民间故事中探索多形态动画
四川阿坝地区的羌族流传着《燃比娃盗火》的民间故事,讲述了一只在古代人类部落长大的猴子去神山寻找“温暖”的秘密。经过千险,它从“恐惧之兽”口中获得了火源,全身着火。它在火中脱发,涅槃成人。羌族聚集地分散在深山里。这个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燃比娃偷火》不会有文字记录。它在民间流传。不同村庄的版本会有不同的细节,但主线是猴子偷火,成年人洗澡的故事。
导演李文愉在羌族地区采风时听到了“燃比娃”的故事。作为一名动画老师,他记得上个世纪,上海美国电影工厂不断将中国不同民族的民间故事改编成动画短片,其中一部发生在云南的盗火主题短片叫《火童》。正如他所感慨的那样,普罗米修斯盗火的主题是全世界民间故事的主题。在柏林影展期间,动画长片《燃比娃》播出时,现场观众大多是本地儿童,儿童反馈热烈。被成年观众质疑的“弱故事线”,其实降低了这部电影的接受门槛,让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沉浸在电影中各种动画情趣中,包括定格、手绘、剪纸、刺绣等。
李文愉有一个大胆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动画长片的工业化水平已经很高了,突出的是制作水平,被称赞为描述类型片框架中的“大场面奇观”,但很少形成动画语言的识别。相反,中国的动画短片聚焦于这种艺术形式,这使得动画短片更容易“成功出海”。因此,他更注重在简单的民间故事中探索多样化的动画语言,不仅继承了中国水墨动画,还融入了实验动画的技巧,同时拼贴了中西合璧的元素,如漫画、拼贴画、装饰艺术等。他承认,这种创作思路挑战了商业电影的惯性。如果没有上海美国电影工厂的支持,《燃比娃》是不可能拍成动画片的。
在不同版本的“燃比娃”故事中,有西南地区的神灵崇拜和民间哲学。动画淡化了与人类学和民族志有关的深度内容,简化为“燃比娃的成长”。关键是把“成长”的内心感受变得具体可视。从猴子到人的进化过程中,“燃比娃”学会了用手和工具,直到创造工具。他最初使用的工具是石头,所以电影用石头制作定格动画来展示这个过程。图像的基调一开始是黑白纯色,后续的颜色逐渐丰富。当“燃比娃”经历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少年往事,值得反复回忆时,画面变成了明亮的剪纸动画。经过对羌族艺术的研究,导演发现,这个民族最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就是羌绣。在电影中,他将羌绣的元素融入到电影中,用羌绣来呈现草原和花海,这段画面大量参照羌绣的传统图案和常见色彩搭配。当“燃比娃”第一次爬行时,它的形象是原始的洞穴壁画风格。随着它离人越来越近,它的肖像依次变成了古埃及和古希腊的风格。直到印象派和当代装饰艺术特色,导演用“燃比娃”的雕像变化,安排了一段简洁的艺术史演变。
导演不回避电影在柏林播出后的评价是有争议的。他认为艺术是主观的,每个人的经历和观点也是如此。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这是一部作品被接受的正常状态。重要的是尽可能多的人看到,让不同的人发现,中国动画长片的表达和中国故事的讲述应该是百花齐放。(报告记者 柳青)
)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