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个星期的秘书:“叙事的困境”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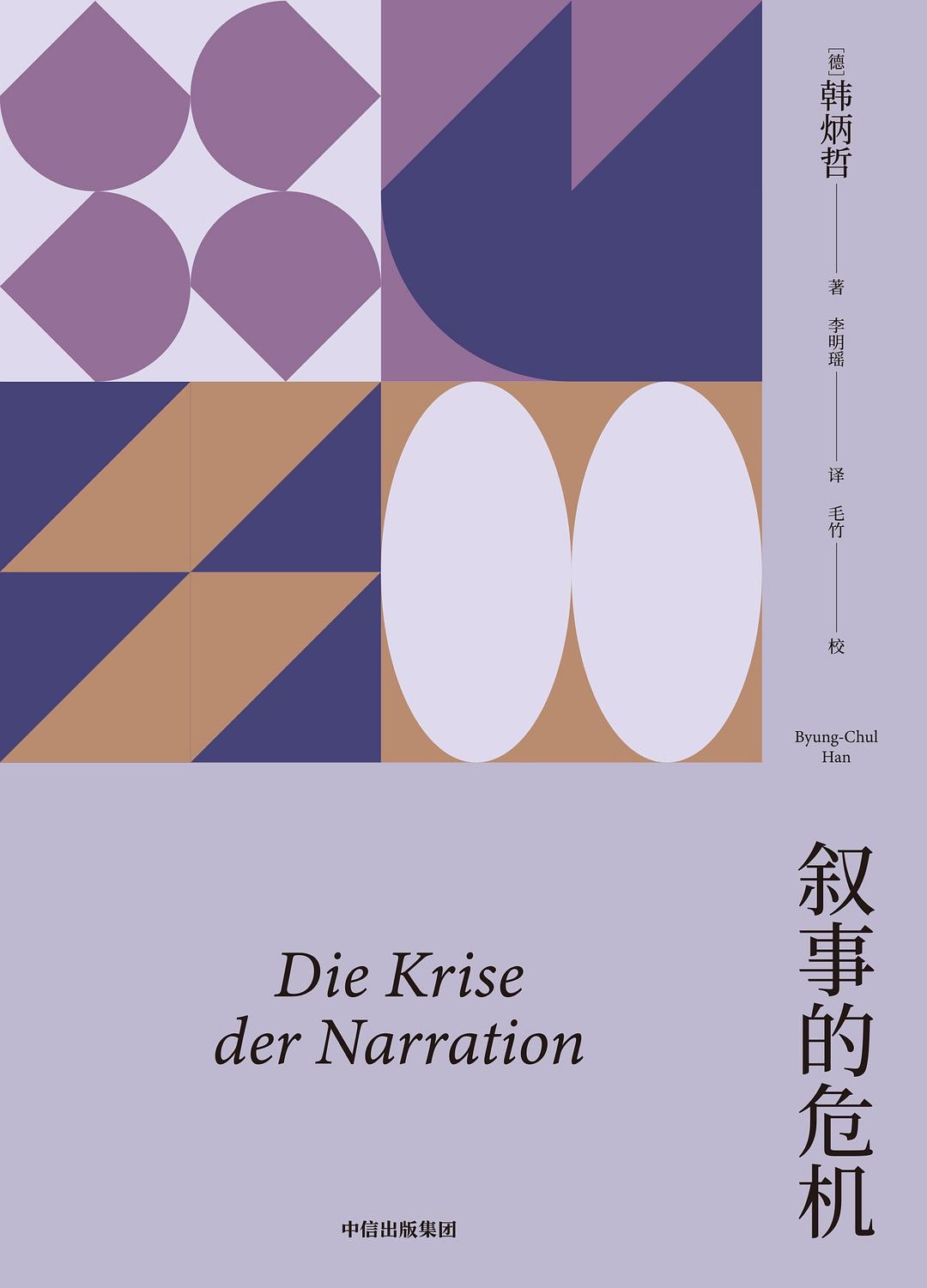
《叙事危机》,韩炳哲,李明瑶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5月版,112页,48.00元,
韩炳哲,德国学者(Byung-Chul Han)在《叙事危机》(Die Krise der Narration,中信出版社李明瑶译,2024年5月)的“前言”从一开始就指出了这本书的主题:“今天是一个大家都在讨论和叙述的时代。不同之处在于,叙事主题的泛滥竟然暴露了一场叙事困境。一种既无意义又无角度的叙事真空,充满了“故事化”的喧嚣。“(第三页)作者在整本书的阐述中不断深入探讨的“叙事困境”是双重的:信息时代造成的叙事困境和故事时代造成的叙事困境,困境产生于信息和故事时代的潮流中。
然而,在这部以“叙事困境”为研究主题的作品中,作者并没有对下一个明确的“叙事困境”的概念定义和解释。自然,我们不会进入叙事学。(narratology)“叙述和叙述结构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感知”等专业路径所形成的“困境”等问题。事实上,所谓的“叙事困境”当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韩炳哲在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天主教神学,他被瓦尔特·本雅明接受。(Walter Benjamin)对叙述困境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篇短篇大论中,他不断引用和诠释本雅明关于“讲故事的人”和世界的去魅力等问题的思想。叙事文学的死给本雅明带来的个人震惊,发展成了韩炳哲,成为对时代病态的揭露和批判。最初本雅明面临着复制技术和大众报刊的全面崛起,叙事文学的“光环”(aura)渐渐退休;今日韩炳哲要呼吁的是抵御“叙事困境”造成的人类精神家园的沦丧。可以说,意识到叙事困境带来的担忧比任何概念定义都更真实,概念解读绝对不是应对信息泛滥和故事化带来的“叙事困境”的最佳策略。
然而,我们不禁要注意到,韩炳哲论述中概念的运用实际上具有不同的语义。翻译后,更容易在中文阅读中获得理解上的歧义。因此,翻译在“注释”中解释了韩炳哲使用的“故事”的概念:“在这本书里,韩炳哲区分了‘故事’对应不同的德语单词。Geschichte既有‘故事’又有‘历史’的含义,与Story相比,Story更符合信息的特点,所以‘讲故事’更符合信息的特点。(Geschichtenerzählen)比‘故事化’要好。(Storytelling)的。Erzählung 意思是‘叙述’,也有‘故事’的意思,从词源上看,erzählen有列举的意思,更注重“计算”(zählen)相对照。为了避免混淆,本书中存在的Story,译者都使用了添加引号的‘故事’,并添加了原文。Erzä大多数情况下,hlung翻译成‘叙述’,有时根据前后文翻译成‘故事’。erzählen多翻译成‘讲故事’。翻译不能体现德语单词的内涵或可能导致混淆的地方,都加了原文。"(前言,第8页)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译者的处理是必要的。
在“前言”部分,韩炳哲对“叙事困境”的描述大致如下: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在谈论叙事的时代,一个让叙事和叙事失去了生命真谛和凝聚力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后叙事时代。(postnarrative Zeit)。在后叙事时代,叙事的魔力耗尽,叙事变得偶然、可替代、可变,不再具有约束力和连接共同体的功能。有意思的是,作者将宗教叙述视为“具有内在真理瞬间的独特叙述”:他说:“基督教是一种元叙事,它涵盖了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并把它引向存在。时间本身就是叙事性的。基督历使每一天都显得有意义。但在后叙事时代,它被剥夺了叙事性,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时间表。宗教节日是叙事的亮点和高潮。没有故事,就没有节日和节日时间,也没有节日感,也就是更深层次的存在感,只有工作和休闲,生产和消费。“(同上,第四页)关于宗教的叙事性在基督教视觉艺术传统中表现突出,通过视觉图像向信徒传达时间和事件的叙事性效果远胜于文字。进入世俗化和后叙事时代后,“节日被商业化,成为事件和景观”(同上)。然后,进一步区分“叙事”和“故事化”的本质区别:“叙事创造了共同体(Gemeinschaft),而且故事化只催生了社区(Community)。社区是由消费者组成的一种商品方式。任何一种故事化的方式,都不能重新点燃那团让人们聚在一起,互相讲述故事的篝火。篝火早已灭绝。代替篝火的数字屏幕,将人们独立作为客户。顾客是孤独的,不会形成共同体。社交平台上的‘故事’(Storys)叙事真空也不能消除。这只不过是色情的自我呈现或个人广告。消费主义行为,如发帖、点赞、分享等,加剧了叙事困境。”(第5-6页)
可以说,就像韩炳哲被翻译成中国翻译的其他十几部作品一样,这部《叙事危机》也有现实前沿,将哲学思维与写作文本贴近数字媒体时代,将哲学的人文传统与批判传统相结合,讨论当下世界的精神状态的基本特征。他被媒体称为“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和“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评指南”是不合理的。但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他的着作在这个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和受到他猛烈攻击的喜爱和赞美的社会中受到读者的追捧和赞扬。难道不会让他一些不乏思想和批判的讨论被同化和扭曲吗?作者似乎不担心成为“网络名人”。事实上,他愿意阅读,有能力理解一位来自本雅明和海德格尔精神世界的东方学者。毕竟人是有限的。“叙事困境”这样的“叙事”原本是危机中的警世之音。另一方面,作者对确定和阐述这个主题的重要性充满信心:“信息海啸的冲击唤醒了人们对意义、同一性和目标性的需求,即让我们面临迷失的信息密林变得清晰。目前,包括阴谋论在内的瞬间叙述和信息海啸,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生活在信息和数据的海洋中,正在寻找叙事的锚点。"(第7页)无论“寻找叙事锚地”的说法是否正确或深刻,后真相时代那种焦虑的感觉的确让人振作起来。
此外,就像我读过的韩炳哲的其他书籍一样,他的批判性总是指向西方社会的现实情况。无论是讨论“今天的痛苦”还是“叙事困境”,都是指从新自由主义的繁荣时代到今天各种裂变困境中的西方社会。基本上,它仍然是一个有纪律的、有压制力的社会背景,没有触及它。关于“叙事困境”的社会语境也指向了新的自由主义:“在新的自由主义制度下,共同体的叙述明显分散,成为自我实现模式的个人叙述。为了提高绩效和生产力,新自由主义独立了人,阻碍了共同体叙述的形成,导致我们极度缺乏能够创造共同体和价值的叙述。过旺的个人叙事使共同体受到腐蚀。“个人故事”在社交网络上与自我展示无关,严重破坏了政治的公共性。(Öffentlichkeit),讲述共同体的形成增加了困难。以叙述为前提的纯粹意义上的政治行动,换句话说,它必须是可以描述的。如果没有叙述,行动就会衰退为任何行动或反应。"(82页)这是在阅读韩炳哲对当前世界的批判性阐述时必须注意的情境问题。当他说“这种叙事困境由来已久,本书将探索其根源”(前言,第8页)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了解她描述的危机及其来源的具体情况。
上述两个问题似乎都不是他的责任,但对于不同语境的读者来说,他们不禁意识到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妥协社会:今日之痛”(吴琼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指出,右翼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最大的危险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极权主义和数字监控技术的结合,使人们面临“一种生命政治监控政权”(71页)。在韩炳哲的思想光谱中,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基本的倾向,但是《叙事危机》基本上并没有涉及到这种观察和攻击的角度。当涉及到信息传递、言论表达、权力和权利的描述、社区的构成原则等问题时,关于什么是“叙事困境”的“最大危险”、它最具侵蚀性的“来源”到底在哪里等问题应该是不可避免的。
在作者的阐述中,我们选择了一段话来讨论:“资本主义借助故事化把叙述据为己有。使叙述听命于消费。故事化创造了一个消费形式的故事。借助故事,商品被赋予了情感,并向消费者承诺了独特的体验。这样,我们的买卖、消费实际上就是叙述和情感。“故事”被推销,故事实际上是卖故事的。(Storyselling)。叙述与信息完全相反。强化信息的随机性体验,叙述将随机性转化为必然性,从而减少随机性体验。信息没有存在的强度。所以,存在的缺失,对存在的遗忘,是信息社会固有的。信息量只能叠加和积累,没有任何意义。叙述是意义的载体。意义本来就是指方向。今天我们确实接触到了极其丰富的信息,但是却迷失了方向。“(前言,第六页)这是作者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信息”和“叙述”的观察和攻击,也经常被引用在一些文章中介绍和评论这本书。在这里,我们对消费社会中的信息和叙述有启发性,但由于情况的不同,我们可能需要思考另一种从韩炳哲版本转换而来的解释:训练权利利用故事化,把叙事和故事据为己有,让叙事和故事听从训练权;我们必须高度统一叙述和信息,加强信息叙述。并将叙述中的随机性判断为不可避免;信息的叠加和积累只能是同质同源的,只能承载承诺的意义;每个人确实可以接触到被允许的极其丰富的信息,然后只知道承诺的方向。
事实上,当韩炳哲不小心向哲学和学校解释时,版本的转换自然会出现:“一旦哲学以科学为荣,甚至以精准的科学为荣,它的衰落就开始了,因为它否定了它最初的叙述意义,所以它失去了语言,陷入了沉默。学校式哲学不遗余力地‘管理’哲学史,这种哲学是无法讲述的。这根本不是一种冒险行动,而是一种官僚机构。面临着当前的叙事困境,哲学领域也未能幸免于难,面临着终结的威胁。再也不敢面对哲学,面对理论,自然也就失去了叙述的气魄。“(68-69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韩炳哲从“叙事困境”的角度转向哲学困境,提出了关于危机的叙事问题——当哲学试图拥有官僚机构的权威时,它最大的困境就会到来;如何描述这样的困境,显然是重新回归真实叙事和叙事的重要性。
关于“讲故事”,这是从本雅明延伸到韩炳哲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少讲故事。(Geschichten)。信息化交流成为一种交流方式,使讲故事严重受阻。很少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讲故事。通过提高共情能力,故事将人们联系在一起。故事创造了一个共同体。智能化手机时代共情的丧失,充分说明智能手机并非讲故事的媒介。"(第7页)"社交网络上的‘故事’(Storys)实际上只是让人陷入独立的自我呈现。相反,它们既不会产生近端,也不会产生共情。归根结底,他们是视觉上装饰过的信息,接收后会迅速消失;他们不讲故事,只做广告。追寻关注并不能创造共同体。叙事与广告在故事化即卖故事的时代是分不开的。那就是当前的叙事困境。"(77页)把“讲故事”作为人类相处和建立认同感的基本途径,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关于当今时代是否越来越少讲故事,需要讲什么故事,一方面取决于对什么是“故事”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不同社会语境中“讲故事”的空间问题。
在“讲故事”这个话题上,韩炳哲并没有像谈到政治行动和叙事关系时那样引用汉娜·阿伦特的思想,从而将“讲故事”的情境和价值延伸到更需要去的地区,这让人觉得有点遗憾。因为韩炳哲引用的阿伦特把政治行动和叙述看作是“总能形成一个故事”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阿伦特关于“讲故事”的重要思想。重视“讲故事”与政治和自由有关。(story-telling),它是阿伦特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在传统的哲学表达方式中,她始终认为人类经验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很难表达出来,只有在“讲故事”的文学资源中才能实现。她特别指出,试图用“独裁”的古典政治概念来理解极权主义,必然会有扭曲这一现象的极端原创性风险。从现有的理论和哲学体系来解释它们是极其困难的(西蒙·斯威夫特 2018年,第4页,陈高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阿伦特导读) 。可以说,阿伦特对“讲故事”的重视与她需要处理的念兹在兹的核心话题密切相关——揭示历史创伤和抵御现实政治的罪恶。意大利作家普莱默·莱维·西蒙·斯威夫特(Primo Levi,作为对阿伦特“讲故事”的“介绍”,1919-1987)在回忆中讲述了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与同屋犯人的对话。斯威夫特认为,如果我们抽象地讲述莱维的故事,我们无法想象意义和力量是一样的。甚至任何简单的解读都会损害故事的复杂性和细微性。 那就是阿伦特“讲故事”的真谛:你不能把讨论政治的阿伦特和讲故事的阿伦特分开。面对前所未有的残酷、新颖、独特和复杂的纳粹极权主义,她不相信仅凭概念、定义和推理的规律就能揭示和表达清楚。即使在对纳粹分子的审判中,她也不能完全相信司法系统的合法性和智力,而更愿意相信记者、诗人和历史学家——历史的古老语义是“讲故事”。阿伦特是一位作家和诗人,从生活经历、政治和真理、历史和创伤的角度来看,他肯定“讲故事”。在阿伦特之后,捷克成为著名的作家,思想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对 “讲故事”也做了深刻的讨论,他指出有一个制度“本质上(原则上)是对故事的敌意”。在监狱里,他发现几乎每个囚犯都有一个独特的、令人震惊或兴奋的生活故事,哲学故事证明了一种叛逆:独特的人性用叛逆来抵御自己的虚荣心;并用自己顽强的精神忽略了消极的压力。在监狱里,他发现几乎每个囚犯都有一个独特的、令人震惊或兴奋的生活故事,哲学故事证明了一种叛逆:独特的人性用叛逆来抵御自己的虚荣心;并且用自己顽强的精神忽略了消极的压力。在他看来,故事是抵御权力统治的有力武器,所以我们必须讲述那些故事——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类命运的故事。
韩炳哲对讲故事的阐述可以说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性意义:“现在连政治家都知道卖故事的重要性。……叙述就这样被政治工具化了。问题的焦点不再是理性,而是情感。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交际技巧,故事化绝不是一种面向未来、赋予人们意义和视角的政治愿景。政治性叙述的意义在于承诺事物的新秩序,描述可能的世界。现在我们缺少的正是对未来的叙述带给我们希望。在各种困境中,我们转过身来。解决问题的政治削减。只有叙述才能打开未来。“叙述”是开启未来的唯一途径,因为“叙述有‘重新开始’的力量。在叙述的前提下,任何改变世界的行动” (87页)。这个问题也需要韩炳哲关于“生命即叙述”。人类作为一种描述动物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可以通过描述来理解新的生活方式。
在这本书的最后,韩炳哲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关于困难的故事:“在一个以故事为导向的世界里,一切都变成了消费,导致我们对不同的叙述、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感知和现实视而不见。这就是故事时代的叙事困境。”(同上)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克服“不同的叙事、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感知和现实”的屏蔽,以及如何描述那些故事。

在欧洲,柏林遇害犹太纪念碑 纸本彩墨 李公明 作 2024年11月4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