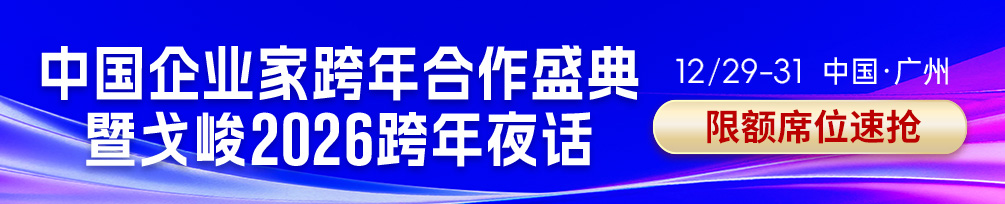三三:南市区长余音

今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一时兴起,骑自行车去外滩看黄浦江。在外滩周围,自行车禁行区划得非常广泛。我远远地下了车,走进了这个曾经很熟悉的地方,突然意识到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景点了。
我从外滩北边的尽头上堤,紧邻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往前看见陈毅雕像。小时候带我来闲逛的老一辈长辈,都去世了,这多少增强了我“过客”的感觉。在黄浦江上,游轮比以前更加密集。广告牌悬挂在它们的顶部,花枝招展,却无法长久地抓住观看的目光。一切都令人眼花缭乱,这个夜晚的世界是由光的猎弹打通的。站在河岸上,我突然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一方面,眼力所能及的地方,纷纷浮现出一种对历史的认识。比如外滩作为“远东第一城市”的中心,有很多看似壮丽的西洋建筑:曾经拥有世界上最长酒吧台的英国上海总会,很多小说中描绘的沙逊大厦,以报时钟著称的海关大楼等等...这些景观见证了上海百年的发展,它们从时间中屹立不倒。另外一方面,当我看着黄浦江彩绘般的水面,凝聚在此时此刻,一种强烈的感觉泛起。“此刻”不同于过去的任何时候,它是时间横截面上最独特的一块。夜晚渗透到水的形状,幻化,流变,无数的概率同时存在于最小的时间单位中。历史与此时此刻,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并行于同一个目光之中。

这种经历让我感叹。我意识到自己正以多种方式与外滩联系在一起。另外,它也是童年生活的地方。
我最早的家位于十六浦港口周围。坐在家里,有时候听到一声低沉的声音,只有港口船只的鸣笛。20世纪90年代,我经常去港口玩。不止一次,我看到很多人拖着行李上岸。我跳到石墩上,观察人流,判断他们在上海会有什么情况——这是一种孤独孩子的心理游戏。
那时,巷子里的房子多么狭窄,三个人住在一起,常常觉得空间不够。幸运的是,邻里之间的交流相当热闹。那时候离上港俱乐部成立还很远,上海只有申花队。每当遇到足球比赛,每个人都会聚集在某个家庭,一起欢呼或辱骂。葱蒜,总能问隔壁借的,哪一户人家多借不还,虽然背后有人嘟囔,确实发生了什么事,还是会有邻居帮忙。白日,我爬下陡峭的木梯,穿过天井,到门口悠闲地坐着。记得一位老太奶奶,诸位老人中,我最接近她。那时候说不出什么理由,只觉得她可怜。多年后才知道,是她身上的死亡气息震撼了我。我无法阻止自己友好相待,虽然有温暖的成分,但大多是为了缓解对死亡的恐惧。临终前一周,她给了我一枚金币巧克力,这是她唯一给我的东西,我把它拿在手里,感受它的重量。我猜到了它的来源,剥去了外面一半的金锡纸,然后原封不动地包起来。很快就听到了她的死讯,它让我长期陷入了愧疚和不安。后来看了侯孝贤的《童年往事》,阿孝的奶奶常常让我想起她。
物资匮乏的阶段,也许很快就会结束。掐指算来,1998 2008年,我们搬出了这所房子,拆下了曾经让整个小巷羡慕的空调。很多旧东西,丢在房子里,等着有需要的人去拿。我还留下了一些东西,比如五岁生日带的珍珠项链,当然是假的。我把它留在那里,不是因为它破旧,而是因为它的告别。为了前进,放下曾经重要的东西。例如爸爸为我做了一顶博士帽,它来自于装满水果的纸箱,尺规画,然后裁剪,涂成黑色。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殷切的期待是多么动人——动人,因为它很有可能会被辜负,而制作它的人知道这一点,仍然认真投入其中。
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爸爸给我做博士帽的细节。小说叫《百合学家》,写得很早,2015年 2000年。这部小说增加了一些虚构的树枝,写道父亲从学校偷了两支黑色记号笔,但他仍然没有足够的时间戴上整个医生帽。因此,我不得不转身,在拍照时把没有画的区域藏在后面。这些虚构的延伸隐藏了我当时对父亲的关注。
然而,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一位在港口边长大的作者,或者是这两年。以前那个地区属于“南城区”,后来因为城市建设的变化而融入黄浦区。但是,南市区的特色却难以磨灭。这里,最豪华的建筑与最脏乱的阴沟共存,当地人和外国人彼此不分。日夜流水不舍,黄浦江对岸高楼迅速迭起,将上海发展中的时间秩序浓缩在其中。一切都是神奇的,令人兴奋,令人激动,也令人失望,在浩瀚的新世界里,无法抓住自己的小剪影。
春节期间,因为和朋友录制了一个播客,想聊聊以前的南市区,我们特意预约了一个。 city walk。在找到过去的家之前,朋友引路。从法律上讲,该地区已经被拆除,但还没有完全拆除。隔着院墙,我尽力凝视着里面的建筑,却一点也不熟悉。它真的站在眼前,却与记忆无关。穿过古城公园,我们走进一条小路。我跟朋友说,小时候外婆经常带我去大境阁上香。朋友们说,大境阁就在路的尽头,旁边似乎还有一个道观。我们匆匆而去,却遇到了关门的大境阁。多么像一个传奇故事,收益《世说新语》也无妨。外婆大约是 2005 20世纪90年代末去世,生病后卧床数年,所以上香多发生在90年代末。外婆信佛,但信得较浅,更像是对“善”的憧憬。那时和她一起去大境阁,一个个凝视着菩萨,我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愿望。要是我的命运,我就接受它。所以我暗中对菩萨说,希望菩萨们事事顺心。沧海桑田,只有二十多年。
童年就像琥珀铂一样,被封在时空的阻隔中。有了写作,我偶尔能感受到再次回归的秘密。英语中,对面的烟纸店,已经拆除的沪南电影院,盛夏推门进时闻到中药香味和凉意的童涵春堂...所有最微妙的末节都可以重现。消失的上海和眼前昂扬的上海是如此迷人。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