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中心的人”:文化诞生的时刻
站在被锯齿形群山环绕的腹地上,十几条地平线相互交错,光源在如此复杂的空间里的明暗变化也会欺骗我们,不再能帮助人们正确感知时间。走在里面,对空间和时间的感受会被颠覆——所以路人会无休止地循环和犯错。恶劣的自然环境压制着人们,人们互相压制——所以人们无休止地分离和战斗,历史无休止地循环和犯错。
2024年3月27日,经典小说《大地中心的人》,上海文艺出版社。
童末在《大地中心的人》开场时写道:行进在山中,“光明与黑暗”都在“互相攻防”。那就是统辖腹地人——也就是“大地中心人”——的古老原则。而且,这座位于中国西南腹地的山地世界“匹配”(彝族对大凉山地区的传统称谓),是世界的缩影。这个世界循环往复地犯错,走到了末世。这部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时刻不同人的行动。
在末世,一个线性时间概念下的词。在小说中,“地球中心的人”/诺苏(自称凉山彝族)的语言中没有“末世”的概念。他们用的词是“斯涅”:死亡日。相应的是“卓涅”:生日。卓涅在斯涅之后,斯涅在卓涅之后可能会再次发生。在这种认知中,时间是非线性的、循环的,人与世界的命运是轮回的。
作者绘制的路线图之一。
对《大地中心的人》进行外封,加上作者绘制的三条路线图,读者得到了一张书中世界的地图。不同于按比例缩小的平面图,不同于官方发行的通用地图,不同于历史某个阶段某个真实存在的地图。这是一张从“地球中心的人”的角度绘制的地图,一张结合记忆、情感、想象和幻想的地图。它既有经验,又有超验。这是父权制顺序最底层的逃亡者:被驱逐的诺苏女性和被掠夺的汉族男性一起走出的逃亡路线图,也是诺苏知识分子毕摩(巫师)传承下来的灵魂的行走路线图,是各行各业军马的行军地图,是“恶魔”俄切的寻金路线图,是故事中相信孜孜尼(鬼母、故事、语言或希望)的人心中世界的真实形象。这种多维度的现实在这张地图上结合在一起,共存,平行交叉,相互争论,相互生成。
那就是《大地中心的人》所呈现的世界。
斯涅
斯涅是书中所有人物共同面对的灾难和苦难,所以所有人物都在逃亡。
随着人物的出现,我们会看到一个流血的世界:在匹配的山区,诺苏人有明确的社会阶层,黑骨头(贵族)和白骨头(平民)肯定是对立的,不能结婚。底层是单身的呷西(奴隶)。家支(宗族)在阶级下面。父母之间有血仇,后人将永远背负着复仇的命运。所以很少有人能活到中年。书中故事发生在旧中国阶段,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山区土地少,难以生存。诺苏男人出去找的“生意”其实就是抢劫。到了山外汉家地段,就成了祸端。它还为当时的“熙夷”政策提供了口实。
事实上,诺苏人的祖先大多是为了逃避战争、饥荒、税收和中央集权的统治而深入的。他们原本是逃亡者和自由者,但现在他们来到了斯涅。根本原因是诺苏社会遵循古老的规则,就像山外世界一样:父权制。
《地球中心的人》的几位主角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和逃亡者。第一个出场的铁哈无疑位于权力序列的底部。由于他是守边熙熙攘攘的汉家军人的孩子,他是诺苏人的奴隶,或者说,奴隶里的奴隶。在被诺苏人打败之后,爸爸想要自杀。诺苏人救了他,收养了他的作家奴隶,名字由冯世海改为铁哈。那是他的第一个斯涅。十几年后,他把被移交给了另一个诺苏家支,这个诺苏家支与主人家为世仇。那是他再次面对的斯涅。所以他踏上了逃亡之路,但是无论诺苏还是汉族社会,都没有他可以容身的地方。最终,他到达了一座被诺苏人视为“鬼地”的德布洛莫洞穴。
第二个主角孜那是诺苏黑骨头人的女儿。她原本是一个高贵的人,因为爱上了白骨头的年轻人而被流放,她的爱人也被罚下了悬崖。孜那坚持用诺苏人的方式安抚爱人的死亡,但很难实现。这个安提戈涅般的角色,因为她坚持用心理准则挑战社会法则,走向了她的斯涅。 最终,她到达了德布洛莫山洞。
第3个主要角色甚至没有名字。他被称为“兹莫闺女”。兹莫作为一个血统高贵的统治者,却不能给自己的女儿起个名字,因为后者是个病人。得了疟疾的兹莫闺女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女人,被隔离在其他地方。感染者经常发高烧,使她趋于通灵。她相信诺苏人鬼母孜孜尼的第一个神话。所以,当她看见两个人影出现在德布洛莫山洞口时,她坚信是孜孜尼第一次回来。所以也来到了洞里。后来,一群像垃圾一样被诺苏社会排出的妇女畸零也来到了这里。
《地球中心的人》内封。
到目前为止,故事中所有赤裸裸的生命都聚集在这里。女人唱着“没有希望”的歌,在这里结盟。然而,这些人只是最有希望的人。他们决心以孜孜尼的力量跨越自己的“斯涅”,这也是诺苏人的共同点,打开“卓涅”,彻底颠倒和更新世界。
洞穴(或炼狱,或母亲,或语言,或莫比乌斯之环)
洞穴也是童末过去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意境。这是一个避难所,一个死亡和再生的母亲,一个文学和虚构相遇的地方。洞穴永远是童末作品中的莫比乌斯之环。
在短篇小说《新大陆》中,异族女主角是一位语言学习者,她曾经“炼狱”(hell)倾听成了“洞穴”(hole)。这个绝不是闲笔。在短篇小说《洞穴》的结尾,历经磨难的女主角被倒塌的煤矿埋在肚子里。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她奇迹般地通过一条狭窄的隧道进入了传说中的地下王国洞穴,被地下河冲回了外界。这一救援过程,仿佛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进入了地狱,又回到了产门,再次被世界子宫分娩。(哪一个世界?真实还是语言?还是两者合一?)这一连接真实与虚构的隧道-洞穴的出现,宣告了作家对知识的信念,以及女权主义者的语言观。
洞穴之旅代表再生。进入地下的死者世界,回归世界,是但丁的《神曲》所描绘的诗人灵魂之旅。只有对知识的信念才能让人完成这次旅行。
在短篇小说《拉乌霍流》中,童末表达了对这种信仰的动人追求和深刻思考。自小病魔缠身的女主角被语言世界拯救,获得了通感的能力,却在恢复健康后背叛了这种不能被外界和自己接受的气场。对知识的热爱就像深刻的记忆,驱使她成为人类学和语言学者,追寻一种濒临灭绝的古代苗族语言。但是,语言工作的范式在田野里总是左右为难。最终,主人公在神启时刻认识到,她所追求的古老语言是一种属灵的语言,而这正是她曾经拥有却失去的天赋。这是活的,不能被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认知体系所捕捉。在文字和逻辑之前,这种属灵的语言只存在于声音、表情、姿态和心灵中。这类语言没有文字,却是文字语言的妈妈。
巫师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因为他们背诵了民族史诗和历史传说,并在与鬼神交流的仪式中保存了这种语言。然而,他们使用的语言和传承的知识可能不够古老。
在《地球中心的人》中,德布洛莫被称为鬼地,诺苏死去的灵魂最后一个非自然死亡、违反古代规则的地区,这里的死亡灵魂是无法循环的。因此,这是诺苏人的禁区,令人恐惧。
德布洛莫的洞穴是炼狱,父系神话中的一个粪坑。然而,在作家的书中,它是母系神话的起点。鬼母/女神孜孜尼刚刚摧毁了旧世界/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代表女性的洞穴是一个莫比乌斯之环,它使匹配的山区有时间和空间的轮换,也是一个完全颠倒古代秩序和意义的莫比乌斯之环。
2020年9月,童末第一部小说集《新大陆》,四川文艺出版社/后浪。
在《地球中心的人》中,鬼母孜尼乍并没有出现在巫师念诵的经文和创世神话中。在诺苏人,尤其是女孩的口口相传之间,孜孜尼初神话只存在。因为孜孜尼初神话比巫师传颂的神话系统更古老。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以前的母系社会,被父系社会所不容,所以她的形象在父权视野中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丑陋。在否定她的存在之前,他们用巫术驱逐她,削弱她的力量。
然而,以兹莫闺女为代表的诺苏零余女性对鬼神话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孜孜尼是一个有再生力量的女神。
斯涅是诺苏自己的。知识分子希望拯救它,但是他们所学的知识已经失败了。只有畸零者拉起手,带着无望的希望,用生命牺牲它,用希望重新启动它。在小说中,女人们用对孜孜尼这个失落的女神的信念,召唤出一场大火。这是孜孜尼在信仰中第一次燃起的毁灭和重生之火,也是现实中心飞行员关邈生(另一名逃亡者)坠机燃起的火灾。它阻止了诺苏人屠杀者和军官“恶魔”俄切在洞穴中开采黄金的计划,也让诺苏人巫师恩信从一个保守的知识分子跳过,成为一个不惜牺牲的守护族人的英雄。
这里,现实与虚构“燃烧”融为一体,这是孜孜尼第一次重生的时刻,也是文学诞生的时刻。
行进
孜孜尼的复活指的是一个更平等、更友好、更有救赎概率的时刻,一个女性主义的世界,一个人类最初拥有却最终失去的世界。相信她就是相信人类能够修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与此同时,她也指向一个语言世界,相信她就是相信语言,相信文学,相信希望。但是,只有希望是不够的。正如书中人物所说,“斯涅要靠自己走过去”。
作家们不厌其烦地写人在复杂的山地上行进,在艰难的循环中犯错,进行人物苦难的历史。这个小主题经常出现,仿佛在隐喻一条通往自我的道路。逃亡者铁哈,一个走在边上的离散者,像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的角色一样,完成了几次变形。他走出了一条通往自我的道路:一开始是汉族士兵的后代,然后是诺苏人收养的奴隶,然后是一个回到汉族世界寻找身份的逃亡者和一个伪装的士兵...他是一面面向世界的镜子,不知道自己是谁,直到所有身份都失败。他到达德布洛莫,变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变成了一个空虚的人。
这儿,铁哈与自己的镜像相遇:一位违反诺苏法则的猎手女孩孜那。这位空荡荡的姑娘让他再一次彻底变形:一个情人。这种变形使他完整。之后,他又一次变形:他相信神话,相信语言。在这个故事的最后,铁哈获得了一个新的社会身份:与汉、诺两个世界的语言工作者交流,并且最终拥有一个自我指责的身份:作者。起初,他是这本书里故事的局外人,然后他是相信孜孜尼第一神话的女性集体叙事的记录者。渐渐地,他成为了这本书的作者和叙事者(其中一个)。
从头到尾,铁哈和故事中的女性角色一起用反抗的行动来维持自己的进步。铁哈和兹莫的女儿一起逃离了德布洛莫。当他们来到山外时,他们发现世界并没有重启,战争越来越激烈,“恶魔”的黄金开采计划也付诸行动。甚至,对于他们所经历的故事,也在不断地被扭曲、篡改、删除。假设他们得到了什么,那就是对历史的认识——历史是空的。于是,他们开始讲述这个故事,写出真实的历史。此时,叙述、写作就是抵抗,就是行动,就是重启世界的可能方式。——那是他们自己走过斯涅的方式。
在书中,铁哈并不是唯一一个成长的角色。小说的最后,兹莫的女儿在山洞里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孩子:小索玛。小索玛是孜孜尼第一次破裂后撒在地上的野花的名字。这孩子实际上是文学之子。他的存在就是嘲笑只提供精子的“爸爸”。兹莫闺女在洞察真相的那一刻,从一个把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的传统女性,变成了一个试图塑造新信仰的人。作为部落的守护者,文化传承者,社会阶层的疏通者,诺苏人的心理医生,对巫师恩札。这是诺苏知识分子坚持正典信仰的写照,他令人尊敬和保守。猎人孜那是爱与平等的化身,她一言不发,一直保持着抵抗力,但却是封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他们聚在一起,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本书是由他们的行动共同写的。
文学行动
书中人物的成长过程无疑是自我指责的。对于一些作家来说,文学是关于少数人和少数人,也是关于失去和失去。有些人会成为少数人的作家,有些人永远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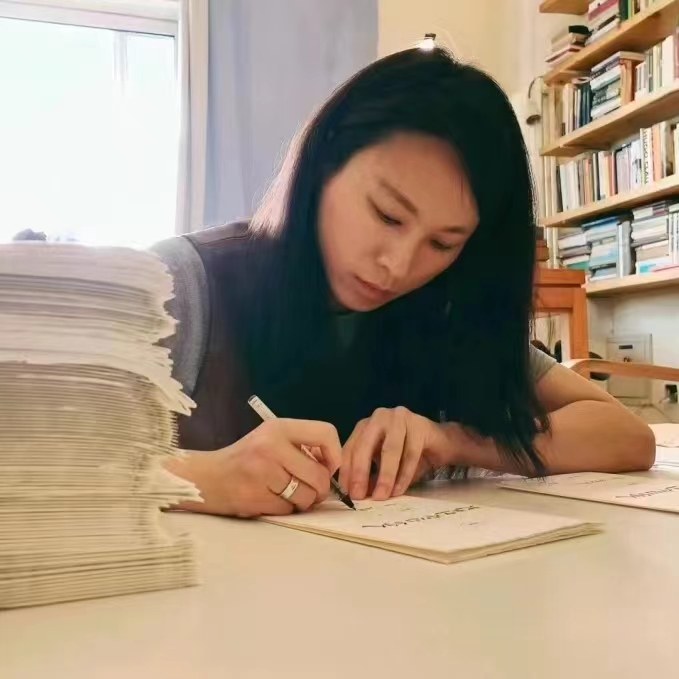
童末
为何选择写凉山彝族的故事?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作家的知识结构、文学观念和价值观的统一。这本书里,少数民族不再是中文作者创造异国风情的景观珍宝柜,也不再是中文作者寄予理想的乌托邦。这本书里,作家们试图和她的写作目标一致,就像孜那和猎食一样。这本书里,他们真的被作者看见了。这是一种灵魂对灵魂的看法,就像故事中那些畸零的人对彼此的看法,女人对孜孜尼的看法。由于这一观点,作者从错误的历史中发现了“踏过谎言和梦想才能到达的真相”。——这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的妈妈”。
假设云贵川是我们的拉丁美洲,那么这本书就是我们的《腹地》和《世界末日之战》。这也让我想起了罗贝托·波拉尼奥对人类文明粪坑的写作,安妮·普鲁对人类和极端环境的写作,科马克·麦卡锡对人类存在的启示录写作,厄休拉·勒古恩对世界的统一制衡写作(包括勇敢频繁使用专名),以及一些百年前的德国作家,比如赫尔曼·布洛赫写的《着魔》,他写的是自然的写作。写约瑟夫·罗特关于历史与人的关系。
其中,战争和战争代理人的书写让人想起了托马斯·品钦对热爱诗歌的军官魏斯曼的端庄戏谑书写——布列瑟罗(死亡)在《万有引力之虹》中的书写。女性的集结斗争让人想起“黑人支队”试图让时间倒流,拯救被殖民者灭绝的部落的故事,希望通过从战场废墟中捡起火箭的零件,以超光速重新组装火箭。当然,这些列表可能不会和童末的阅读重叠,准确的想象总是把作家带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正如童末在后记中所说,她的“老师”之一是凉山彝族送灵仪式上所唱的《指路经》。巫师用语言引导死亡的灵魂,引导死亡的灵魂从家中出发,穿越群山,回到祖国。指路经并非一成不变。几代人的巫师/知识分子不断修改这篇文章,重复神话和历史,这段历史就像希罗多德的《历史》,溶解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这本书里,现实和虚构就是这样融合的,直到德布洛莫的大火点燃,达到顶峰。最终,作为一名女性主义作家,她复活了孜孜尼乍,完成了对《指路经》的重写。
提及上述参考谱系,不仅仅是为了表明《大地中心的人》的立场,更是为了描述它的风格。毕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地球中心的人》采用了一种充满力量、属灵的语言。这就像走在悬崖峭壁上的人的脚步一样谨慎和准确,又像一位天才飞行员,让语言令人叹为观止。它是一种跨学科的写作,混合了文学、人类学、历史、神话学,它的语言也混合了上述各学科的语体特征。或许会带来一些阅读障碍,但是文学应该是开放的。正如书中所说,老毕摩被灌了致幻剂之后,大脑敞开了。他发现脑中所有的知识都失败了。这个时候,他需要向女人学习,向历史妈妈学习。我们也是如此。
所以,下一个斯涅循环,也许我们不会失败。
(作者是南京大学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


